把靜物寫活,誰能比得過這部紀錄片的文案
《如果國寶會說話》這檔節目大家應該有所耳聞,5分鐘左右一集,但內容豐富,解說文案也一直收獲好評,節目更新至第四季。
相較于前三季,第四季的文案稍作創新,結合文物自身風格、故事,敘事角度、形式有所轉變。不變的是,透過文字,我們依然能感受到這些跨越千年物件背后人的溫度,其承載的祝福、哲思和那些最樸素的故事,總是精妙地與現下的某個時刻默契共振。于是,我們透過一件物,窺見了人類歷史長河中文明的流轉,探見了無畏走向未來的精神支點。
本期節選節目10篇解說文案,邀您共同品讀。
01 碗


人類最早的碗就是掬起的雙手,手是靈活,敏感的身體末梢,而碗,則成為手的延伸,端起碗,不過是平凡的日常,放下碗,人類免除饑渴,迎接生命生長。
無數次,我們向碗里探望,用手端起碗,送到唇齒邊飲用,進食。
碗體的材質,碗壁的線條,碗口的厚薄,為我們的身體所感知,有時候我們借助勺子,筷子,幫助水或食物入口,建筑從碗到人的橋梁,撰寫禮儀的法則和傳說。

我們以身體為尺度,不斷重塑碗的形狀和大小。當食物被煮熱,碗底慢慢升高,當碗的容量增加,端碗的手便虎口張開。當我們的眼睛停留在碗的內外,碗就出現了繽紛的裝飾,目力可及的位置,才有描繪或書寫的需要。
永遠中空的碗是為了實現容納,保存了人類感官體驗的歷史,也為了盛放文明的細節。
一萬年過去了,碗還是碗,透過它,我們仍能看見每一個人最真實樸素的生活愿望。
02 枕


初夏,晚涼,這個尚有幾分嬰兒肥的男孩,穿著長袍,套著坎肩,俯臥在榻上。
他的兩臂環抱著,頭歪在上面。他額頭開闊,面部豐滿,唇厚耳大,兩只小腿交叉上翹,手里抓著一支繡球,休閑調皮。床榻的四周,模印著螭龍和如意云頭,男孩就這樣趴在上面,慵懶閑散。
當我們認真地看著他的眼睛,他已經看盡了人間。
定窯,北宋五大名窯之一,定窯的瓷土帶著它來到塵世。
關于孩兒枕的形象,有這樣一種猜測,每到七夕節,宋代的街頭巷尾就會售賣一種造型各異的人形玩偶,被稱為“磨喝樂”。《東京夢華錄》中有這樣的描寫:七夕前三五日,小兒需買新荷葉執之,蓋笑顰“磨喝樂”。這樣習俗一直流傳了很長時間。

也有人說,“磨喝樂”是“羅睺羅的訛傳,而羅睺羅則是佛陀的孩子。
佛陀的孩子,或許這就是宋人眼中的他們。
他們是生命的本源,是我們的天性,充滿無數可能。
他有時候化現為步入迷途時指點迷津的童子,有時又化現為悠閑自在時偶遇的道風仙骨的牧童。

他們在松樹下,他們在月光中,他們在溪澗旁,他們就是我們的小時候。
社會多元,文化繁榮,經濟富足。
百子圖宇宙中的孩子,在天地的庭院中,在時間與生死的游戲里,盡情盡興地玩耍著,無始無終,無憂無慮。
定窯孩兒枕,生來天真,伴你入夢,與你還童。
03 早春圖

“早春 壬子年郭熙畫”
北宋熙寧五年(1702年),畫家郭熙用小楷落款,加蓋印章。
這幅高大的立軸山水,原本應用于裝飾屏風,或許是汴京宮城里的寵兒。
畫框外,四季周而復始,晝夜交替不盡,已成熙攘鬧市。畫框內,時令未改,封存了宋人心中的一個春日。
山腳下,溪流已解凍,水汽升騰。山澗雜木,正抽出新芽,水聲蕩漾,似能聽見木船觸岸,船夫抬頭眺望,這山仿佛人間的巨物,渾如“天地之骨”。由下而上,高聳的峰嶺穿過縷縷煙云;自前而后,嶙峋的巖石,躲進層層薄霧;自近而遠,極目遠眺,是天地無垠。


在天地間安放身心,師法造化,是他們的靈感源泉。
從俗世到林泉,畫家們的視覺奇跡,全憑胸中萬里氣象。借由畫筆,將山水延續至庭院或堂室,足以“不下堂筵,坐窮泉壑”,臥游神州。
流動的煙靄,溢于屏風的屆框之外,無意間,沾染了主人和賓客的衣襟,也給我們留下一個超越時間的、永恒的春日。
04 玉

一千年前的玉向我們走來,帶著它主人的體溫,我們從未如此接近。
通過一塊玉,彼此握手,你已葉落歸根,塵歸塵土,只有這玉芒,溫暖如初。
春水玉,透閃石材質,由公元10世紀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
器物正面,刻畫一只天鵝,脖頸彎曲成一道弧線,身體漂浮、上升,張開鮮亮的羽毛,恰如一支舞蹈,可細細看去,它的頭頂盤踞一只獵鷹,這是海東青,海東青勾住天鵝的頭皮,尖嘴瞄準了天鵝的雙眼,只消一叨,就可以結束天鵝的生命,天鵝順從而平靜地接受必死的命運,微張開嘴,似乎正發出哀鳴。

玉雕題材的殘酷,暗示著佩戴者生存環境的漂泊。
那時,受季風氣候的影響,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獵的習俗,居無定所,先民們打造弓箭,馴化鷹犬,漁獵山林,制作出以鶻攫天鵝為主題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為主題的秋山玉。
春漁于水,秋獵于山,生于天地,歸于自然 ,這些動物圖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間,縫制在人們的肩袖,成為身體的一部分,風起時,人起舞,把鹿畫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鷹刻在腰間,腰肢就成了天。
他們以海東青自比,歌頌先祖與族人自強不息的精神,這玉佩里曾涌動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體溫,看久了,也會感到溫暖。誰飛翔在天空,又被誰困在玉石中;誰捕捉了天鵝,又被誰捕捉于永恒;誰伸出了爪子,抓住本來就是一體的頭顱;誰張開了翅膀,掠過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風。
生命從未終止,只是不斷開始,那時的獵鷹,墜入此刻的視野它一直在揮動翅膀,一直在飛。
05 漆


歡迎進入這“漆”彩世界,林檎樹枝頭,兩支黃鸝啼鳴,石榴櫻桃為伴,蜻蜓蝴蝶相隨,它們來自明宣德年間,顯現出生機一片。
一個碩大的“春”字,中心盤坐一位壽星,下方寶盆聚寶,光芒四射,這是來自明嘉靖年間的“壽春”圖案,充滿人們祈盼的幸福和平安。

這只造型別致的手爐,是雍正時代的審美,木胎上黑漆描金,描繪了遠山近石,亭臺樓榭,草木飛鳥,細致入微,帶來一絲優雅的溫暖。
它們構筑出一個精巧奇異的漆器世界。剔犀、剔彩、描金,制作手法和主題色彩構成它們的名字,異彩紛呈中,獨有一抹顏色最為燦爛厚重,這就是雕漆剔紅。剔紅,以木為胎,少量也以金屬為胎,在胎骨上髹幾十至上百層的紅漆,以到達一定厚度,描畫稿,雕花紋,經歷累月經年的陰干、打磨,最終成為一簇簇動人的紅。

朱砂如血,松煙似發。從朱砂和松煙,人們得到了兩種漆器最初的主色——紅色、黑色。熱烈與深沉,從原始時期,經春秋、歷戰國、穿秦漢、越唐宋。紅色的漆,就這樣一年又一年,髹飾著古老的國度。這個國度有很多引以為傲的顏色,但只有一種顏色,和這個國家并稱——中國紅,如此準確將中國形容。
06 瓷


雨過天青云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汝窯,影響了后世千年中國人對美的認知。
開片,本是殘缺,在精心的控制下,卻造就了哥窯特殊的美,絲弦之間,形如冰裂、“蟹爪”、“魚子”、“牛毛”,這些不完美的完美,都有自己獨特的名字。

入窯一色,出窯萬彩。如果你愿探索未知,那鈞窯的“窯變”,便是驚心動魄的偶遇。在青料中加入銅鐵,經過氧化與還原的灼燒,形成不同深度的紅紫變化,汝夢幻泡影,汝宇宙洪荒。
“君子比德于玉”,官窯瓷不是玉,而釉色似玉,為追求玉的質感,需層層上釉,也代表著對極致的追求。不計成本,卻為著一種返璞歸真的目的。
天、地、宇宙、人心,宋瓷的意境,藏著中國人心里的乾坤。
07 黃州寒食帖

一千年的時光,化作幾筆墨跡,幾方印泥,密麻麻的圖章,像后人的手指,戳戳點點,那年的筆跡,已成絕響的嘆息。
《黃州寒食帖》是蘇軾政治理想的幻滅,也是東坡率真生命的開始。

懸針,變奏,飛白,牽絲,堆墨,此刻,詩人的肉體極度困頓,精神卻無限飛揚,縱然滿腹經綸,又有幾人落筆無塵,哪怕才高八斗,又有誰出口便是天真?
一千年,東坡已經離去,指尖流淌的文字成為哲人生命的延續,近千年的時光,化作數十克的紙,完成生命意義的提純。
人們念東坡的詩,寫東坡的字,渴望從平凡的生命中超脫,從失意中尋找詩意,可幾人又懂蘇軾,讀懂元豐五年的寒食節,此后一句大江東去,換多少孤枕難眠。
08 宋刻本

我,一只蠹魚。我在地球上已存在三億年,而我的這片領地,其歷史不過一千年。
這里是我的王國,十二條經線,兩條維線,幅員不算遼闊,亦足夠我徜徉。我時常巡視邊界,沿著墨線爬行,偶爾躺平曬個太陽。哦,順便說一句,蠹魚就是書蟲。

我開始重新審視那些方塊字,中縫、卷尾的“世彩”二字,記錄著這書的出版人,廖瑩中家族趟號。相傳,他刻書用墨,“皆雜泥金香麝為之”,奢華文字書寫的,是韓愈的巨作,他是古文運動的發起者。空階一片下,琤若摧瑯玕,干凈簡潔的文筆,沉醉了無數個春風漂浮的夜晚。
最棒的紙,最貴的墨,最美的文筆,讓這本書獲得了宋版書”神品“的美譽。
我思考,漫長的時間里,人類總是愛較勁。他們拿骨頭刻字,劈竹子做簡,鐘鼎文字,制禮作樂。他們繁衍,他們用方塊字描述球形的世界。他們造紙,他們發明印刷術。他們打字,他們廣播,他們接入互聯網,他們語音輸入,他們AI識別,他們飛向太空。
蠹魚啃書變成渣渣,人類啃書化作力量。哎,做人不看書,和蠹魚有什么區別。
09 枯木花吟琴

相傳,琴為伏羲氏所造,琴形如人。古琴的設計使其在樂器中居于至尊地位,時空為基,宇與宙形成的三維時空架構。四方上下謂之宇,往古來今謂之宙,“徽”象征著時間的流動,與七弦形成經緯,以“三分損益”法定音。五音為制,古琴原本是五弦五音,后文王武王各加一弦,其音與宮商相同,高了八度以豐富音域。五行是構成世界的基本方式,是萬物生化發展的規律。

禁徽成律,隔八相生,旋相為宮,十二律不僅定音,也是度量衡的標準。琴的設計主旨即是平衡,小腔體為低音,大腔體為高音,以達中和;木胎揚,灰胎和大漆抑,使得琴聲幽遠而又幽微。
古琴制式合于宇宙的規律,琴音與宇宙運行同頻共振,“樂”即“藥”,修正身心之“樂”,琴樂能正心,亦是療慰身心之藥。
伏羲作琴便為修養心神,返其天真,回歸本性。古琴有一套專屬的減字譜,由文字譜的指法,術語結合簡化而成。很難想象,在人類社會的初始階段,就設計出了載道之器,撫慰和修養著人心,并開啟了綿延幾千年的,中國的禮樂文明。
10 朝元圖

神仙,是什么樣子?
面壁者默然無言,須臾,抬起了握筆的手,線條從筆尖緩緩流出,如江河在大地上綿延伸展,原本空無一物的白墻,轉瞬間滿壁風動,天衣飛揚。傳自唐宋的畫稿中,衣帶依然飄舞,霎那間,如同舞臺帷幕拉起,云開霧散,光滿塵壁。

近三百身神靈,在四百平方米的壁畫舞臺上,各安其位,八位高達三米的帝后,占據隊伍中心位置,帶領圣眾前來朝謁原始天尊,這便是被稱為《朝元圖》的景象。
掌管著天地萬物與塵世禍福的神仙們,都有著人的模樣。
此時,太陽和月亮,不再輪流登場,而是并肩同行,五星,緊跟在日月身后,在這里,他們化為文官、武將、老翁和少女。熟悉的北斗七星,則擁有了年輕、英俊的容顏。頭頂上的群星沉默無言,卻成了人們眼中性格各異的老幼男女。

忽然間電閃雷鳴,便與令人生畏的角色四目相對,北方四圣,身形魁梧,面容獰厲,仿佛一頓足、一怒吼,大地就要為之震顫。大地上的眾神,也未缺席盛會,五岳均身著帝王冕服,莊重與威嚴并存。

而當我們的目光,與一件道袍上的仙山相遇時,才驚覺,剛才所仰望的山川神靈,只是戲臺上的扮演者。畫家像是指揮者,行筆或輕快流暢,或頓挫有力,造就了顧盼生輝的面容,迎風飄舞的長線,和諧典雅的色彩,演繹者令人沉醉而又似曾相似的瞬間。

龐大的隊伍,在時空中穩步前行,如天地運轉,萬物以息相吹。
雖然一切都如同畫家創造的戲劇,我們依然聽見人間的衣裙飄舞,也聽見了宇宙的呼吸。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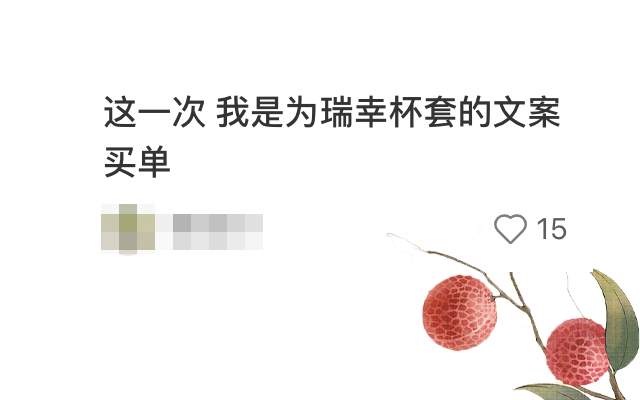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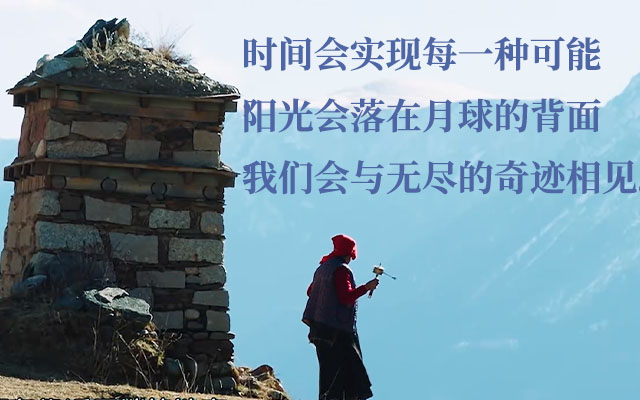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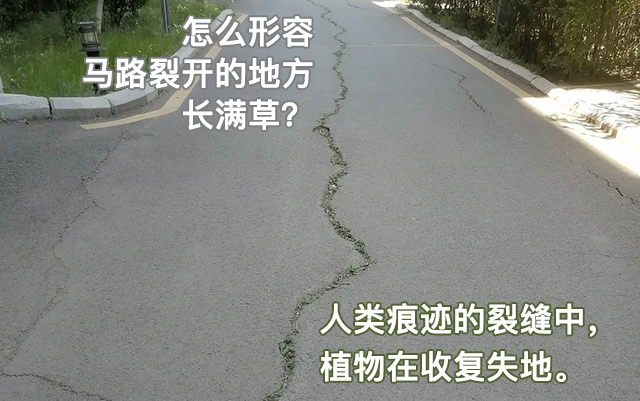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1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