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掘背后: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只花150萬拍攝,收獲無數好評

拍攝條件的拮據、故宮本身的厚重歷史、修復師的日常和觀眾眼中的“匠心”,都匯聚到了這樣一部故宮博物院周年紀錄片里。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B站地址:戳我
原標題:故宮博物院 90 周年拍紀錄片,從前到后也就花了 150 萬
毫不意外,《我在故宮修文物》是一部窮嗖嗖的紀錄片。
攝制組連導演一共 5 人,連拍帶剪 7 個月,以每集 50 分鐘的長度在央視紀錄片頻道播出,算是開年新節目。一般來說,紀錄片的每分鐘成本基本在 2 至 3 萬元,以這部片子的播放總長 150 分鐘算,怎么也得拿個 400 萬上下的錢,但它的總投資不過 150 萬元。
這幾乎是所有紀錄片面臨的窘境。中國電影市場已經走到了它歷史上的最高位,但紀錄片的行情乃至整個行業的狀況并沒有太多本質上的進展。《我在故宮修文物》導演葉君引了一句話:“紀錄片只能說是個行業,還不是產業。”而他自己的說法是:“我就希望這個片子有人看。”

然而這部窮嗖嗖的紀錄片卻獲得了意外的好口碑。它在愛奇藝播出時,有條彈幕總是從觀眾眼前飛過:“這簡直是故宮的招聘廣告,好嗎!”
雖然豆瓣主頁評價人數不到 4500 人,但是總分高達 9.5 分——就算算上觀眾給的情懷分,這也算得上是一個相當好的評價。很多人說它“很燃”,考慮到它的鏡頭解說都是那種慢悠悠的節奏,“燃”這個字基本上指的是那些最近被說得很俗的東西:工匠精神,或者說,“匠心”。



也幸虧了這些東西,這部紀錄片才得以問世。它能夠順利拍完播出,是因為參與者或多或少懷揣著各種各樣非正式的目的,有些甚至和藝術無關,可以算是“憐憫”。
《我在故宮修文物》是為了配合故宮博物院 90 周年院慶拍攝的,故宮出場地,也提供被拍攝者和題材。它說的是一群文物修復師的故事,不過導演沒有把語境設定在“文物專家”這種嚴肅的調調上,而是增加了類似于修復師們逗貓、打杏子、抽煙、騎著電動車跑來跑去的場景,甚至還有修木器的修復師回中央美院參加同學聚會的段落。


故宮博物院審片的時候希望把這些生活段落拿掉,因為害怕外界覺得他們沒有好好工作,好在制片人雷建軍和監制徐歡最終說服了他們。
這些日常和故宮博物院本身的博大悠久放在一起,形成了一種奇妙的反差。這或許是后續好評如潮的原因之一:它不端著。那些文物在這種日常的語境里獲得了特殊的真實感,它不再是存在于玻璃柜后面的一個陳列品,而是被拍攝者生活的一部分。
就好像紀錄片里史連倉師傅說的“御棗遷出故宮”一樣,他其實就是準備把故宮里一棵棗樹的幼枝送給朋友扦插。陶瓷組的紀東歌在故宮里騎自行車,因為她上班需要去另一個地方,片子的旁白說:“以前在皇宮里能像她這么騎自行車的,估計只有溥儀。”


很多人“花癡”鐘表組的王津,有一次他去故宮的鐘表展,看到那些安靜地陳列在那里的鐘表,說自己有點心疼。“這些鐘表本來需要動起來的,報時啊,裝飾機關啊。”紀錄片里它們真的動起來的時候,彈幕滿屏,大家都說“美哭了”。


這部紀錄片得以在央視播出,可能是因為監制徐歡,他本身是央視紀錄片頻道的一位導演。作為合作方,央視僅僅提供了播出渠道,沒有出資。
為《我在故宮修文物》提供資金的,是一個叫蕭寒的人。他最早是個主持人,現在在浙江工業大學任教,也拍一些紀錄片。關于拍攝成本,按照蕭寒對《好奇心日報》的說法,那些錢最初都是他投的,片子收尾后,陸續又有人加入,跟他分攤了投資。
而拍紀錄片的,是清華大學的清影工作室。這是清華大學新聞學院的一個組織,其實算不上是個公司,可以理解為類似于圍棋協會、插花協會那樣的機構。制片人雷建軍、導演葉君都來自這里,還有很多清華大學新聞學院的學生也參與了粗剪。至于拍攝,都是他們從外面找來的。
主創人員是對故宮有了解的。雷建軍和徐歡在 2011 年合作過紀錄片《故宮 100》,可能是因為這個淵源,《我在故宮修文物》也是這兩個人在立項、調查和籌款。生于 1983 年的導演葉君,同樣也參與過《故宮 100》的拍攝。
葉君對《好奇心日報》說,拍攝這部紀錄片,他有一個特別大的訴求,就是向自己的親戚朋友解釋自己的職業:第一,他希望人看這部紀錄片的時候能看得下去,看的時候覺得愉悅,看完后覺得有趣,有個回味。第二,他想告訴別人,他的這份職業,能帶給他什么快樂、什么煩惱。
葉君說,他在拍《故宮 100》的時候見過那些好東西,而現在故宮文物的修復總是面臨著沿習和改革,科技越來越厲害,傳統和現代沖突變大的時候,這樣的題材本來就有戲。
“我們是背唐詩宋詞長大的,但是坐著地鐵,用著微信。我們是有傳統,但還是現代的人。”他拍攝時還給一些文物拍了照片,不過自配了 OS,比如把一個番人進寶柜子上的小場景配上了“還錢”。
還錢!

放學你別走

如果真要細究這些文物的意義,可能就是修復佛像的屈峰說的話:“文物其實跟人是一樣的,中國古代人講究格物,就是以自身來觀物,又以物來觀自己。”很多人在看完紀錄片后都記住了這句話。
相比情懷,《我在故宮修文物》的剪輯和配音得到的好評要少得多。盡管葉君說他參考了法國經典影片《紅白藍》的敘事方式,以“麻花”的結構讓元素交織在一起,還是有評論說“粗糙”和“不舒服”。
至于配音,清影工作室最后找來了《魯豫有約》的制片人曹志雄來配。他是制片人雷建軍大學時的上鋪,聲音又比較有現代感。在此之前,他們還找過的有《飛魚秀》的主持人小飛,因為他有點害羞,最終沒用那個版本。還有臺灣演員金士杰,因為住院了,沒能來。還有李健、吳秀波、徐崢,他們都因為時間不合適沒能來。
有很多人在吐槽這個配音,說是發音不標準,n 和 l 不分。葉君覺得沒問題,“侯孝賢拍過一部臺北故宮的紀錄片,叫做《盛世里的工匠技藝》,那配音是侯孝賢自己配的。字正腔圓的未必就好。”
鑒于審查和篇幅限制,每一集的片子從最早的 90 分鐘一集到 60 分鐘一集,再縮減到 50 分鐘一集。葉君說,60 分鐘其實是最好的,那樣片子可以有一些留白,有個“松口氣的地方”。
紀錄片剪輯時葉君寫的備忘錄

一些復雜的主題也一起被剪掉了,比如修復師們曾經在修文物的時候討論過這些文物是留在中國更利于保存,還是當年被入侵的外國人帶去國外更利于保存。
有一個沒有拍的場景是,修復師們從不加班,因為擔心注意力不集中損傷文物。但他們被規定早上 8 點按時上班。一些修復師住得很遠,早上來上班需要換 5 種交通工具。葉君開玩笑地說,他倒挺希望這片子能讓修復師和拍紀錄片的都漲點工資。
修復師的工作備忘錄

到 2016 年 1 月底,只有愛奇藝和鳳凰視頻買下《我在故宮修文物》的版權。出品方說每一家為版權付出的金額是 5 位數,且遠遠不到 10 萬元。而 B 站上早就有了高清資源,再多出幾家估計可能性也不大。他們也沒計劃拍續集,但蕭寒說,也許拍攝“故宮大電影”是有可能的,只是這個要看“機緣”。
2015 年,除去真人秀電影,中國過審上映的紀錄片一共為 8 部,總票房 3150 萬,算是比往年有了長足進步。在電視領域,收入最高的莫過于《舌尖上的中國》,據說總收入高達 3 億元。紀錄片在全球范圍內都是小動作,但能夠關注它的人群素質本身相當不錯。這一點在探索頻道創始人亨德里克斯的自傳《探索好奇》里有長篇的論述,這位創始人說,探索頻道之所以可以成功,因為他在一個科學統計文獻里讀到"地球上的成年人里面,大約還有 25% 能保持好奇心"。而紀錄片,就是一個被好奇心驅動的生意。
看起來,《我在故宮修文物》還是以 150 萬元的投資和不到 10 萬元的收入結尾了。但蕭寒說成本至少能收回一半,他還有繼續出售版權的機會,一些電視臺也在購買版權的接洽,素材還可以繼續賣錢。
說到紀錄片這個市場,葉君拿菜系打了個比方,“這個市場應該有湘菜也應該有粵菜,但是現在湘菜館子到處都是,沒有粵菜館子。那想吃粵菜的人,也就沒有地方了。”
紀錄片《我在故宮修文物》B站地址:戳我
關于「好奇心日報」:
qdaily.com — 把世界變成問號。每日報道與你有關的商業新聞,無論它是科技、設計、營銷、娛樂還是生活方式。另外還有一個“生活研究所”供你吐槽生活。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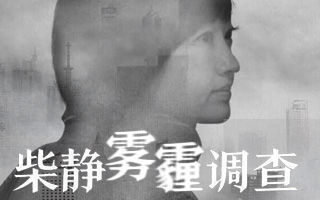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1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