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后北漂的人生:有人三戰(zhàn)考研,有人為愛(ài)負(fù)債,有人無(wú)奈離開(kāi)

作者:姚米力
編輯:楊真心
90后逐步“老去”,95后正走向臺(tái)前。
這些95后新面孔,對(duì)于外界來(lái)說(shuō)多少有些陌生,但在他們的身上,人們依舊能夠找到一些自己的影子,尤其對(duì)于那些在外漂泊尋找夢(mèng)想的人,比如“北漂”、“滬漂”。
“飄向北方、別問(wèn)我家鄉(xiāng),高聳古老的城墻,擋不住憂傷”,黃志明的《飄向北方》這樣刻畫著北漂人的內(nèi)心,而那些正在從不同地市、四面八方加入到北漂行列的95后,他們的內(nèi)心怎么想的,此刻又在經(jīng)歷些什么?
2020年末尾,我們采訪了四位95后北漂,聊了聊他們的北漂生活,以及未來(lái)與夢(mèng)想。
他們當(dāng)中,長(zhǎng)沙女孩程穎,此時(shí)正在憑借著“主播”這個(gè)新興職業(yè),走在上升的快速通道,盡管這被很多人認(rèn)為是吃青春飯,但程穎卻希望在北京,通過(guò)主播圓夢(mèng)娛樂(lè)圈。
95年的豆豆作為一名畢業(yè)生,和很多同齡人一樣,試圖通過(guò)考研留在北京這個(gè)城市,實(shí)現(xiàn)自己的電影夢(mèng),但這已經(jīng)是她第三次考研了,她說(shuō),25歲還年輕,還可以再任性最后一把。
大熊是一名新媒體小編,因?yàn)殚T檻低、再加上疫情,他必須要在激烈的競(jìng)爭(zhēng)中找到自己的出路,最終事與愿違,甚至還因?yàn)椤懊ず小边@個(gè)用于減壓的愛(ài)好,欠了一筆“巨款”,他說(shuō)現(xiàn)在只想把欠的錢還清,過(guò)個(gè)沒(méi)有負(fù)擔(dān)的年。
吳磊是四個(gè)人當(dāng)中唯一一個(gè)選擇離開(kāi)的年輕人,在北京生活5年之后感到厭倦,他打算遠(yuǎn)地離開(kāi)這個(gè)城市,而讓他灰心的,是讓很多人都頭疼的房子問(wèn)題,但不同的是,他還有很多人所沒(méi)有的退路。
豆豆,95年,學(xué)生
第三次考研,北京就是我的電影夢(mèng)
我今年25歲,畢業(yè)兩年了,今年是我第三次考研。
2018年,大四,還沒(méi)畢業(yè),在學(xué)校里考的第一次,考的導(dǎo)演系。現(xiàn)在回想起來(lái),那時(shí)候根本沒(méi)有做好充足準(zhǔn)備。當(dāng)時(shí)其實(shí)沒(méi)有跨專業(yè)考研的經(jīng)驗(yàn),以為自己平時(shí)對(duì)電影足夠了解了,心態(tài)上還沒(méi)有那么重視。
那次考的成績(jī)其實(shí)總分不低,英語(yǔ)政治我都很認(rèn)真復(fù)習(xí)了,但專業(yè)課的分?jǐn)?shù)沒(méi)有過(guò)線。我的室友們好像對(duì)這個(gè)結(jié)果一點(diǎn)都不意外,因?yàn)槲覐囊粋€(gè)普通211一本的中文系,想要考進(jìn)最好的電影學(xué)院的導(dǎo)演系,在他們看來(lái),就是不可能。但我成績(jī)一直不錯(cuò),從小就是個(gè)非常認(rèn)真學(xué)習(xí)的孩子,我就是想試試。
那時(shí)候,我的三個(gè)室友,分別一個(gè)拿到了一所香港大學(xué)的offer,其余兩個(gè)人分別在老家和上海找到了工作。就只剩我一個(gè)人,沒(méi)有結(jié)局,沒(méi)有出路。
第二年,我沒(méi)別的想法,就是還想試一次。我想,第一次是專業(yè)準(zhǔn)備不夠充分,但這次我有經(jīng)驗(yàn)了。努力真的有回報(bào)吧,我初試真的了分?jǐn)?shù)線,國(guó)家線,學(xué)校的線都過(guò)了。
但誰(shuí)也沒(méi)想到我會(huì)卡在復(fù)試上。現(xiàn)在回過(guò)頭去看,也不知道哪里出了問(wèn)題。我覺(jué)得是命運(yùn),差不多300個(gè)人爭(zhēng)奪一個(gè)名額,我又是個(gè)普通學(xué)校中文專業(yè)的,可能我的確不是導(dǎo)師們的優(yōu)先級(jí)選擇。
我考研的初衷,是因?yàn)槲掖髮W(xué)學(xué)的并不是我自己喜歡的專業(yè)。我想學(xué)電影,但是當(dāng)年選擇了中文系。一個(gè)中文系的人畢業(yè)了,接觸到的大部分工作機(jī)會(huì)還是一些文職工作,做做策劃、行政這些。
我其實(shí)一直沒(méi)有去實(shí)習(xí)過(guò),別人在實(shí)習(xí)的時(shí)候我就在準(zhǔn)備我的電影考試。但是我其實(shí)可以想象,一個(gè)中文系的普通人以后如果不能成為作家,就大概率會(huì)淪為一個(gè)每天打卡上班的邊緣崗位白領(lǐng)。我認(rèn)識(shí)的一個(gè)同專業(yè)師姐,畢業(yè)之后在一家快消品公司做市場(chǎng)的工作,她經(jīng)常跟我抱怨,工作日復(fù)一日,疲勞且枯燥。
這不是我想要的,我想創(chuàng)作,想留在北京,離我喜歡的電影近一些。我覺(jué)得考上一個(gè)還不錯(cuò)可以學(xué)電影的學(xué)校,在北京這樣的可以討論文藝大城市,是讓我接觸到這個(gè)行業(yè)最快的途徑。
第一年沒(méi)考上,我父母都沒(méi)說(shuō)什么。他們其實(shí)很支持我,因?yàn)橐灿X(jué)得追求我喜歡的沒(méi)什么錯(cuò)。但是我第二年還沒(méi)考上之后,我媽有一天突然跟我商量,要不要先找份工作,或者考個(gè)公務(wù)員。

我知道她是為我好,但當(dāng)時(shí)其實(shí)還是很受傷。那是我第一次動(dòng)搖,是不是還要堅(jiān)持下去。其實(shí)我這兩年復(fù)習(xí),最大的壓力都不是復(fù)習(xí)考試這件事本身,最大的壓力是我覺(jué)得我自己成年了還在啃老。
我甚至覺(jué)得親戚們是不是都在背后議論我。我老家在山東,還是很傳統(tǒng)的。大家更喜歡畢業(yè)有穩(wěn)定工作的人,小縣城里的人也不會(huì)在意你是不是追求夢(mèng)想。
后來(lái)我為了不讓爸媽覺(jué)得壓力大,也是為了自己短暫的逃避吧,我就聯(lián)系我在北京工作的一個(gè)同學(xué),借住到她家里,然后在北京,一邊做一些兼職一邊復(fù)習(xí)考試。來(lái)北京,也好像是斷了自己后路,一種必須要留下的決心。
我來(lái)北京之后,只去過(guò)我夢(mèng)想的那個(gè)學(xué)校一次。去那次,是為了聽(tīng)一個(gè)講座,也是為了讓我更堅(jiān)定一下,去看看,在我理想的學(xué)校里,大家都過(guò)著什么樣的生活。
今年考試已經(jīng)結(jié)束了。我心態(tài)已經(jīng)比較平淡了,前兩次每次考完名單都沒(méi)有我,最難受的時(shí)候其實(shí)已經(jīng)過(guò)去了。我知道,年輕啊,夢(mèng)想這些很虛,可能我的人生也未必會(huì)因?yàn)榭佳谐晒Χ惺裁创蟮母淖儯揖椭皇窍胱龀蛇@件事。
這一年,除了在兼職的時(shí)間,我?guī)缀趺刻靸牲c(diǎn)一線,在家附近的一個(gè)咖啡館和我的小床上穿梭。7點(diǎn)起床,12點(diǎn)睡覺(jué),上午復(fù)習(xí)英語(yǔ)政治,下午復(fù)習(xí)專業(yè)課,生活的軌跡都被框在固定的時(shí)間內(nèi)。
有時(shí)候我想,只是不想那么輕易認(rèn)命吧。但是,如果明年出了成績(jī),結(jié)果還是沒(méi)考上,我就要認(rèn)真考慮是否要去工作了。大家都說(shuō)事不過(guò)三,這三次,的確我的能量也消耗的不剩多少了。
25歲之前我還年輕,還可以趁著青春任性一下;25歲之后,我可能也要考慮面包的問(wèn)題了。
程穎,98年,帶貨主播
帶著一個(gè)明星夢(mèng)到北京做女主播
我叫程穎,22歲,去年專科畢業(yè)之后,來(lái)到北京。我上的專科是學(xué)護(hù)理,當(dāng)時(shí)成績(jī)不好,只想找個(gè)學(xué)校上,并不是自己真的喜歡。但我喜歡化妝,喜歡打扮,從小就喜歡。我爸媽也很支持我。
我為什么想要來(lái)北京?其實(shí)就是想到大城市闖蕩。我家在湖南,讀書(shū)也一直在那里,從小就沒(méi)離開(kāi)過(guò)。我很想到北京看看。當(dāng)然更深層的原因,是我心里還有個(gè)明星夢(mèng)。
我畢業(yè)的時(shí)候,看到一個(gè)MCN招聘主播,我就跟我爸爸要了幾千塊錢,一個(gè)人來(lái)了北京。那時(shí)候其實(shí)覺(jué)得主播好像不難,就是做到鏡頭前,化妝,賣東西,我覺(jué)得自己可以試試。
我們公司其實(shí)是買了幾百個(gè)種子,都給他們澆水,看最后哪一個(gè)能長(zhǎng)成樹(shù)。一個(gè)運(yùn)營(yíng)負(fù)責(zé)七八個(gè)主播,給我們基本的培訓(xùn),教你怎么在鏡頭前表現(xiàn),然后幫著找一個(gè)定位,你就可以自己回家,到出租的房子里開(kāi)播就行。
我的定位就是可愛(ài)的小女生,教大家化妝的同時(shí)帶一些化妝品的貨。
第一場(chǎng)直播,我還記得,面前六個(gè)燈,光線直射,晃得人睜不開(kāi)眼。但其實(shí)很快,眼睛就習(xí)慣了這個(gè)光。直播前選好衣服,假發(fā)、配飾通通戴好;清點(diǎn)好直播中會(huì)用到的東西,提前上架要用到的鏈接。然后想清楚今天給大家化個(gè)什么妝,怎么賣那些產(chǎn)品,就可以開(kāi)始。

一場(chǎng)直播一般是6個(gè)小時(shí)起步。第一次特別慘,4個(gè)小時(shí),100多個(gè)人看,什么也沒(méi)賣出去。
下播之后我非常失落,我發(fā)現(xiàn)看著很簡(jiǎn)單的事情,但做起來(lái)并不簡(jiǎn)單。我不知道在鏡頭前說(shuō)什么,也沒(méi)經(jīng)驗(yàn),要去跟觀眾互動(dòng),只知道表演化妝。
還沒(méi)有辦法,只能一點(diǎn)點(diǎn)的進(jìn)步。前10天是最痛苦的,100人、200人,直播間人數(shù)增長(zhǎng)少得可憐。轉(zhuǎn)變就是突然發(fā)生的。有一天,不知道是誰(shuí)最早發(fā)現(xiàn)了這個(gè)入口,成千上萬(wàn)的觀看人流涌進(jìn)我的直播間里。
我還記得,那一次,彈幕特別快的一條一條閃過(guò),在某一瞬間,其實(shí)我很慌。但是很快,我就跟每條彈幕都互動(dòng)。從那天起,幾乎每天不落,完成到現(xiàn)在完成了超過(guò)300多場(chǎng)直播,最多的時(shí)候一場(chǎng)直播有十幾萬(wàn)人觀看。
從19年底直播到現(xiàn)在,我的粉絲有11萬(wàn)多了。每月帶貨也差不多能有十幾萬(wàn)到小幾十萬(wàn)的流水。
雖然公司和平臺(tái)還是拿最大的分成,但是大部分時(shí)間,我的收入都能保持在3萬(wàn)以上,有時(shí)候達(dá)到5萬(wàn)或者8萬(wàn)。我非常滿足了,因?yàn)槲蚁胛疫€是沒(méi)有做這個(gè)選擇,而是在老家找了一份護(hù)理相關(guān)的工作,那我的收入可能只是現(xiàn)在的十分之一。
其實(shí)很辛苦,覺(jué)得時(shí)長(zhǎng)不夠,就想從4小時(shí)到6個(gè)小時(shí)再到8個(gè)小時(shí)。有時(shí)候,是真的嗓子啞了還繼續(xù)直播。下播之后其實(shí)也辛苦,你必須足夠?qū)I(yè),粉絲才可能留下。不直播的時(shí)候我都在學(xué)化妝,學(xué)穿搭。
另外就是去進(jìn)行一些接近表演的培訓(xùn),我覺(jué)得我不能光靠個(gè)性留住一點(diǎn)點(diǎn)粉絲,我想吸引更多的人進(jìn)來(lái)我的直播間,我要學(xué)會(huì)鏡頭前更自然的展現(xiàn)自己。
有人說(shuō)主播是吃青春飯的,我一點(diǎn)也不贊同這種說(shuō)法。我和粉絲之間其實(shí)有很牢固的感情,說(shuō)白了,他們?cè)敢饪次业闹辈ィ铋_(kāi)始是為了學(xué)化妝知識(shí),但時(shí)間長(zhǎng)了,他們就是喜歡上了我這個(gè)人。我也會(huì)逐漸有自己的個(gè)人品牌。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播不動(dòng)了,那我覺(jué)得我這些年輕時(shí)候的努力,至少能讓我有資本去做另外的事情,比如可以去嘗試我的明星之路,比如做一個(gè)自己化妝品品牌。我沒(méi)有想太多,這個(gè)行業(yè)會(huì)火多久,主播這個(gè)職業(yè)的前景是什么樣子的,至少目前,它幫助我實(shí)現(xiàn)了我以前不敢想的很多事。
大熊,96年,新媒體編輯
來(lái)北京就為圖個(gè)離家近,卻弄的“負(fù)債累累”
我叫大熊,96年,2019年從廣東一所大學(xué)畢業(yè)。因?yàn)槲沂潜狈饺耍腚x家近一些,所以畢業(yè)之后就來(lái)到北京,找了一份新媒體的工作。
2020年,我的人生關(guān)鍵詞可能就是負(fù)債。前一陣子豆瓣上那個(gè)負(fù)債小組的話題很火,我之前并不怎么玩豆瓣,但是也去看了。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迷戀奢侈品,買鞋買包,或者是為了住更大的房子,吃得、穿得更好。但是我發(fā)現(xiàn),好像像我這樣,因?yàn)橘I盲盒負(fù)債的人的確是少數(shù)。
我畢業(yè)兩年,月薪稅前9000,我不知道這個(gè)工資在我這個(gè)年齡段算怎么樣的,但除去2800的房租和基本的吃穿開(kāi)銷,我原本每月大概能攢下一兩千塊錢。去年年底的時(shí)候,我還給爸媽包了8888塊的紅包,為了慶祝我人生第一年領(lǐng)工資。
原本我來(lái)到北京的原因是為了賺錢,因?yàn)檫@里的工資高,但可能當(dāng)初也沒(méi)想到,伴隨高工資的一定是更大的壓力。
今年我遇到一些新?tīng)顩r。疫情之后,我的工作并沒(méi)有因?yàn)樵诩肄k公而變得輕松。因?yàn)槲沂莻€(gè)做新媒體的,實(shí)際上過(guò)去兩年我?guī)缀醵际菦](méi)有周末,24小時(shí)待命的狀態(tài)。找選題,追熱點(diǎn),碼字,排版,發(fā)送之后運(yùn)營(yíng),這個(gè)流程中的每個(gè)環(huán)節(jié)都能把我搞崩潰。
我其實(shí)在19年底就開(kāi)始意識(shí)到我并不是很適合、很喜歡眼前的這份工作。疫情的到來(lái)加劇了我的這種感覺(jué)。我嘗試換工作——后來(lái)我想了想,這可能是我負(fù)債的導(dǎo)火索。
今年的工作市場(chǎng)并不樂(lè)觀,對(duì)于我這種想要再次從零換一個(gè)崗位的人來(lái)說(shuō),狀況更嚴(yán)重。我想去做一些偏市場(chǎng)營(yíng)銷的工作,但是因?yàn)闆](méi)有相關(guān)的經(jīng)驗(yàn),面試了幾次,沒(méi)有人要我。我實(shí)在想逃出新媒體小編的旋渦,但是無(wú)果。
可能是太苦悶了。壓力特別大,但我又不是那種愿意把這些事情分享給家人的人。我總覺(jué)得男孩要堅(jiān)強(qiáng),遇到事情要自己扛。我在北京也沒(méi)什么朋友,跟同事很難分享這些情緒。而且因?yàn)榭偸亲a字,我的頸椎也經(jīng)常出現(xiàn)問(wèn)題。
總之那段時(shí)間精神和身體雙重崩潰。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買盲盒。周末我一個(gè)人去家附近的商場(chǎng)吃飯,就在大家經(jīng)常可以看到的那種盲盒自助販賣機(jī)前面停住了。最開(kāi)始真的純屬好奇,按鍵、支付,59塊一個(gè),買了倆。
回家拆開(kāi),整個(gè)過(guò)程,真的很解壓。那時(shí)候還沒(méi)有多么迷戀某個(gè)形象的概念,但整個(gè)過(guò)程很期待,很想拆開(kāi)是自己看中的哪一款。
再之后,只要我出門吃飯,路過(guò)商場(chǎng)的時(shí)候基本都會(huì)買幾個(gè)盲盒回家。那時(shí)候我不覺(jué)得會(huì)花太多錢,總覺(jué)得一個(gè)也就幾十塊,一周買個(gè)兩三個(gè)其實(shí)不算啥。第一個(gè)月的時(shí)候大概買了有十幾個(gè)。
隨著我買得多了,我發(fā)現(xiàn),盲盒很多門道。比如有隱藏款,有人按照某個(gè)系列、某個(gè)IP去收藏,還有人二手交易稀有的盲盒賺錢。我開(kāi)始深入研究,開(kāi)始還妄想是不是可以通過(guò)買盲盒,一邊自己爽了,另一邊還可以賺錢。
大概5、6月份開(kāi)始,我開(kāi)始去一些盲盒的專門店里,抱著一種可以“出二手”賺錢的心態(tài),去整個(gè)系列整個(gè)系列的買。
回家拆開(kāi),不喜歡的就掛上閑魚(yú)或者在一些盲盒二手群里出售。買的范圍也開(kāi)始從基礎(chǔ)款盲盒,到一些限量款,藝術(shù)家聯(lián)名款和一些大娃。價(jià)格從最開(kāi)始的幾十塊,到幾百、一兩千。一個(gè)原本幾十塊的盲盒可能被炒到幾百,我還是會(huì)買,因?yàn)橛X(jué)得買回來(lái)可以升值。

我自始至終沒(méi)有過(guò)多的關(guān)注錢這個(gè)問(wèn)題,花了都可以出二手賺回來(lái)。到10月的時(shí)候,我想去外地參加一些潮流玩具的展會(huì),買機(jī)票的時(shí)候,我才發(fā)現(xiàn),自己本來(lái)就不太多的存款,交完三個(gè)月房租,就剩下1000多。
我太想買到展會(huì)上的限量款了。我后來(lái)就在某平臺(tái)借到一萬(wàn)五千塊,買了機(jī)票去了展會(huì)。那次展會(huì)上,我買各種玩具花了8000多,賣掉6000。這其實(shí)更堅(jiān)定了我賣二手可以賺錢的想法。
但是我沒(méi)有想到,能賣出去的還是少數(shù)。而且好像我更喜歡買的過(guò)程,怎么去賣就比較沒(méi)心思經(jīng)營(yíng)了。隨著我買的數(shù)量增加,買到的沒(méi)啥用的也就越來(lái)越多,閑魚(yú)上的成交量卻沒(méi)有相應(yīng)增加。到12月的時(shí)候,我的出租屋里已經(jīng)攢了400多個(gè)盲盒、玩具,其中我舍不得賣,想要收藏的可能也就四五十個(gè)。
我沒(méi)去統(tǒng)計(jì)我一共在盲盒上花了多少錢,但是我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負(fù)債6萬(wàn)了。這其中除了我因?yàn)榉孔獾狡诎崃艘淮渭遥孔鉂q了500塊,大部分的開(kāi)銷還是在玩具上。
我的各種借貸工具上的額度不斷上漲。我現(xiàn)在在三個(gè)不同的借貸產(chǎn)品里分別欠著8000、4萬(wàn),和1萬(wàn)塊,這都還不算它們各自的利息。這半年以來(lái),我和我僅剩的一點(diǎn)工資,就在這些借貸產(chǎn)品不停上漲的額度里循環(huán)。
2020年過(guò)去了,我不僅沒(méi)有換成工作,過(guò)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還陷入一個(gè)奇怪的消費(fèi)怪圈中。我想起來(lái)去年過(guò)年我還給爸媽紅包,今年想的卻變成了怎么能盡快把錢還清。
我的北漂生活就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yīng)。我想換工作,但疫情讓這變得很難,我的壓力很大,恰好盲盒釋放了我的壓力。我至今沒(méi)想明白,我是怎么一步步把這么多錢花掉的。自責(zé)、后悔,這些我都沒(méi)太去想了,我只是覺(jué)得壓力更大了。經(jīng)常睡不著,想著怎么能快點(diǎn)把錢還上,回家過(guò)一個(gè)沒(méi)有負(fù)擔(dān)的年。
我已經(jīng)想辦法把我的公積金里的錢取出來(lái),想再在周末接一些微信寫稿的私活,無(wú)論如何,得靠自己把債還上。我不想新的一年,是從欠債開(kāi)始的。
吳磊,97年,產(chǎn)品經(jīng)理
租房,是讓我離開(kāi)北京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大學(xué)就是在北京讀的,加上工作了一年,今年在北京已經(jīng)第五年了。
其實(shí)留在北京是很順理成章的事情,我是北方人,加上讀書(shū)實(shí)習(xí)都是在北京,找工作的時(shí)候我也比較順利,覺(jué)得至少有了可以留在這個(gè)城市的資格。
但今年這個(gè)短租房暴雷、疫情這些都是壓倒我的稻草,五年來(lái),我正式開(kāi)始嚴(yán)肅考慮離開(kāi)北京的問(wèn)題。
我畢業(yè)之后在一家互聯(lián)網(wǎng)初創(chuàng)公司做產(chǎn)品經(jīng)理,其實(shí)還算不錯(cuò)的工作,同事們?nèi)硕己芎茫业墓べY也算比很多同班同學(xué)都高的。
但是北京的生活壓力太大了。首先擊垮我的,就是租房。上學(xué)的時(shí)候住在學(xué)校,真的不知道大城市生活的殘酷。實(shí)習(xí)還沒(méi)轉(zhuǎn)正的時(shí)候,我就在開(kāi)始找房子。我很想一個(gè)人住,覺(jué)得享受一個(gè)人的空間是工作后最基礎(chǔ)的自由。因?yàn)槲业拇髮W(xué)就已經(jīng)是合租生活,所以我一直都清楚,如果不自己住,生活就是租來(lái)的,根本不由自己控制。
所以很自然的,我把找房子的范圍鎖定在了那些XX公寓上。這些公寓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比合租貴一些,又不是我住不起的一居室整租那么貴。他們通常都經(jīng)過(guò)還不錯(cuò)的裝修,面積不大但五臟俱全。
其實(shí)在它暴雷之前,我一直住的都很舒服。下班回家可以有屬于自己的一塊小天地——直到我所在的短租公寓也暴雷了。
我的房租是押一付一,那個(gè)時(shí)候得知暴雷的消息,其實(shí)已經(jīng)不是錢的問(wèn)題。而是在很短的時(shí)間內(nèi),找到下一個(gè)落腳點(diǎn)。
這時(shí)候才是讓我苦惱的。我平時(shí)工作很忙,其實(shí)并沒(méi)有太多時(shí)間看房子。但我又真的不想將就合租。但是完整的一居室起租價(jià)就是5000多,我根本負(fù)擔(dān)不起。

△北京的老房子
開(kāi)始跟著中介看了幾套房子,周末的時(shí)間幾乎都用在上面,一天能看三套。也有比較合適的,價(jià)格就是最大的門檻。后來(lái),我改變策略了,價(jià)格、房子質(zhì)量和交通,我必須舍棄兩樣。我就選擇了離公司比較遠(yuǎn)的地方,開(kāi)始看那些沒(méi)有電梯的老房子,我想我租過(guò)來(lái)之后,可以自己改造。
就這樣,我在靠近南城,找到一個(gè)一居室,押一付三,月租4300。我最開(kāi)始安慰自己,至少在接受的了的范圍內(nèi)實(shí)現(xiàn)了租房自由,可以有完全屬于自己的空間了,而且也算比較成功躲過(guò)了公寓暴雷的影響。
但好日子沒(méi)過(guò)多久。我經(jīng)常需要加班到十一點(diǎn),十一點(diǎn)沒(méi)有了地鐵,我只能打車回家。我們公司在海淀,我夜里回家的起步價(jià)都是80多。我們初創(chuàng)公司,也沒(méi)有人說(shuō)會(huì)給你報(bào)銷。
早上上班早起,上班路上一個(gè)小時(shí),先騎單車再換乘最難的4號(hào)和10號(hào)線,在地鐵里被擠成肉餅——這些其實(shí)我都忍了。
把我擊潰的是打車的賬單。有兩個(gè)月下來(lái),我一看滴滴賬單,我在打車上花的錢將近2000。除了加班的時(shí)候,白天經(jīng)常出門著急了,也會(huì)打車。我一看到賬單,當(dāng)時(shí)就崩潰了,因?yàn)槲乙粋€(gè)月可能也就能攢2000。
所以我就想,還是得搬家,需要離公司近一點(diǎn)。就又開(kāi)始了新一輪找房子的過(guò)程。這次不光需要找房子,還要把我沒(méi)到期的房子轉(zhuǎn)租出去。我開(kāi)始在豆瓣發(fā)帖子,開(kāi)始聯(lián)系中介,在別人來(lái)看我的房子和我去看房的事情上花了特別多的時(shí)間。
差不多到10月的時(shí)候,我真的累了。我第一次開(kāi)始思考在老家的生活。雖然我家只是個(gè)三線的城市,但也是應(yīng)有盡有。最重要的,有一個(gè)寬敞的家,什么電器都有,有寬敞的客廳和沙發(fā),還有會(huì)給我做好飯的爸媽。
一旦開(kāi)始有這個(gè)想法,我對(duì)找房子的事情就開(kāi)始松懈了。一方面租房真的太累了,耗時(shí)耗力耗錢。另一方面,我的確開(kāi)始渴望在老家過(guò)另一種不需要那么累的生活了。
我思考了回家可能做的工作,回家之后能怎么養(yǎng)活自己,回家之后會(huì)不會(huì)無(wú)聊。給我爸打過(guò)一次電話。我爸爸一輩子都在一個(gè)事業(yè)單位坐辦公室,他一聽(tīng)我的想法就說(shuō),“在外邊累了就回來(lái),離開(kāi)北京也沒(méi)什么可恥的。”
就是我爸爸的這句話,卸下了我腦子里所有的負(fù)擔(dān)。我這才開(kāi)始審視自己,其實(shí)我留在北京幾乎是出于一種慣性,我沒(méi)有想過(guò)這種漂泊、需要特別努力才能活得差不多的生活是不是適合我。
而自我審視了之后,我也才意識(shí)到,我就是想過(guò)一個(gè)小城里的安逸人生。想到這里的時(shí)候,我徹底釋懷了,我不再找房子,跟領(lǐng)導(dǎo)溝通了,年底拿完年終獎(jiǎng)后就會(huì)辭職,我爸會(huì)幫我在老家找一份工作。
2021年2月,春節(jié),我就會(huì)離開(kāi)北京。這一次,就不會(huì)再回來(lái)了。
*應(yīng)采訪對(duì)象要求,豆豆、程穎、大熊、吳磊為化名
*圖片來(lái)自受訪者及網(wǎng)絡(luò)
*版權(quán)聲明:本作品著作權(quán)歸“沸點(diǎn)Point”獨(dú)家所有,授權(quán)深圳市騰訊計(jì)算機(jī)系統(tǒng)有限公司獨(dú)家享有信息網(wǎng)絡(luò)傳播權(quán),任何第三方未經(jīng)授權(quán),不得轉(zhuǎn)載。
轉(zhuǎn)載請(qǐng)?jiān)谖恼麻_(kāi)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hào)(ID: digitaling) 后臺(tái)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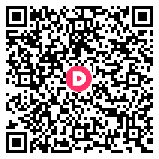

評(píng)論
評(píng)論
推薦評(píng)論
暫無(wú)評(píng)論哦,快來(lái)評(píng)論一下吧!
全部評(píng)論(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