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詞人姚謙:我一直在堅持手寫,每個字都是我的選擇
來源:三明治(公眾號ID:china30s
原標題:寫詞人姚謙:我一直用手寫,堅持每個字都是我選定的 | 寫作者訪談
作者:李依蔓
本文經授權發(fā)布,轉載請聯(lián)系作者
姚謙說自己是個有長性的人,從入行到2005年離開,在唱片行業(yè)一做就是將近20年。
但如果在26歲那年,姚謙拿到的第一份offer不是來自唱片公司,他也許會成為一名編輯或電影工作者,名字不會在華語流行樂壇中占一席,和李玟、蕭亞軒、王力宏、蔡健雅聯(lián)系在一起。
1987年,姚謙離開自己的第一份工作——汽車公司展示員,經過半年的休養(yǎng),踏上了一場四天的獨自徒步旅行。他在旅行中決定自己未來想要進入的領域是出版社、電影、音樂三選一,隨便哪個都可以,跑腿打雜也可以。所以假設進了出版社或電影行業(yè),姚謙也有極大可能會一頭扎進去,做個幾十年。
那一年他沒想過自己會寫歌詞,會因為一項兩個小時完成的電影《魯冰花》配樂工作而獲得臺灣金馬獎最佳電影插曲獎,會成為索尼唱片、維京唱片的高管,會被媒體冠上“最懂女人心的寫詞人”稱號。不過姚謙有些無奈。據粗略統(tǒng)計,姚謙曾為至少130名歌手寫過歌詞,其中超過三分之一是男歌手,但大家似乎都只記得他寫“女人歌”。

姚謙在1987年來到臺北,那一年唱了40多首廣告金曲的周華健嶄露頭角,鄧麗君發(fā)行了她的最后一張國語專輯《我只在乎你》。第二年,雖然蔣經國逝世讓臺灣娛樂業(yè)蕭條了一個月,但在黨禁、報禁開放的文化利好背景下,臺灣唱片業(yè)迅速發(fā)展,光是下半年的唱片銷量就達到前兩年的銷售總和。
誤打誤撞地闖進音樂圈,踩上了臺灣唱片行業(yè)產業(yè)化節(jié)點的姚謙,從每天“傻開心”、什么都做的唱片業(yè)學徒,轉型成為一名專業(yè)寫詞人、制作人,沿著唱片產業(yè)巨型齒輪壓出的印痕越走越深。
2005年,姚謙從維京唱片離職,離開唱片行業(yè),進入“半退休”狀態(tài)。他見證了唱片業(yè)平地而起,盛極一時,又在互聯(lián)網沖擊下日益衰頹的起落變化,留下超過600首歌詞,包括流行音樂、音樂劇、電影配樂。
成為“自由人”的十年里,姚謙的詞寫得少,更多是應邀撰寫隨筆和專欄,關于情感、藝術、旅行。
談及寫作內容的變化,姚謙這么寫道:
“當真實生活的質量及不上書寫的數量,創(chuàng)作與謊言只是一線之差。創(chuàng)作若沒有名與利的負擔,也沒有屈于怕被遺忘的廉價自尊之下,那才是一種自由。當我不斷地這么告訴自己時,歌的完成量減少了,生活的質量卻漸增。旅行、閱讀、嘗試錯誤,都是值得書寫的生活。書寫有了意義,讓我有種又活過來的存在感。”
2017年7月,姚謙出版了自己人生中的第六本書。和之前所有的歌詞、隨筆一樣,這本19萬字作品集里收錄的文章,都是姚謙在平板電腦上用食指寫完的。電子產品的技術進步,并沒有改變姚謙的寫作習慣,不過讓他從用筆在紙上寫,變成用食指通過手寫輸入法在屏幕里上寫而已。
“寫下哪個字,就是我選擇了哪個字,不然用其他輸入法會跳出很多相關的字,會打亂你的思路。”
姚謙很固執(zhí)。
出版社為姚謙安排了七場新書發(fā)布會,第一場在北京。姚謙記得自己第一次到北京時,住在長安街邊上的一個酒店里,他竟然沒有異鄉(xiāng)感,覺得自己回到了放大了好多好多倍的小時候生活的眷村。
在那個小小的村落里,男人們都是從大陸到臺灣的軍人,姚謙的爸爸來自浙江,對面的周伯伯來自湖南,每次家里要炒辣椒時總會提前告知鄰居,小心被嗆。他記得如果要吃饅頭,一定要去村子另一頭山東叔叔家。他記得牽著媽媽的手,到眷村其他嫁給大陸軍人的臺灣本地太太家里,和她們的孩子一起打發(fā)炎熱又漫長的臺南午后。
在6歲到25歲之間,姚謙幾乎沒有離開過臺南。

臺南出了許多文藝人,比如李安、侯孝賢、魏德勝。臺南還是許多影像的背景元素,是《童年往事》里阿孝咕的祖母尋找與大陸家鄉(xiāng)相似的風景,是《冬冬的假期》里一個見識成人世界各色面孔的童年暑假。臺南也是姚謙希望花筆墨去書寫的記憶之地,他懷念那個30臺幣就能連續(xù)看兩場電影,被西方電影和文學喂養(yǎng)的少年時代。
三明治和姚謙聊了聊,這位從臺南走到臺北的文藝人,這位同時身為寫詞人和專欄作家的寫作者日常。

陰差陽錯,進入唱片行業(yè)
三明治:你是一個從小對文字、閱讀就有興趣的人嗎?
姚謙:小時候我就很愛看書,臺灣有個兒童刊物叫《國語日報》,上面有四格漫畫,比如小亨利,有用兒童口吻寫的新聞文章,有作家介紹、科學知識。報紙上有注音符號,不認識字也可以用注音符號去讀通意思。
當時以我父母的薪水來說,訂這個刊物是有負擔的事,因為他們會訂一段停一段時間,停之前他們會告訴我,下個月沒有了喔,以后有錢再訂。我知道沒辦法,所以每次要停掉的最后那幾天,我就會特別渴望,很珍惜。
停訂的有一天,我記得我在門口眼巴巴看著送報員過去,對他笑,結果他停下來,把報紙給我看,因為他知道我之前經常訂,他就等我。我拿過報紙快速地看,突然我媽看到我在門口,可能是怕我耽誤人家,讓我快回去,我就把報紙趕緊還給他。
三明治:小時候有什么特別的閱讀偏好嗎?
姚謙:小學五年級我們家搬到臺南縣,那時候個性比較活潑,認識了一個純粹的臺灣人,以前在眷村長大,認識的全是眷村的小孩子。他家境很好,家里高學歷、有產業(yè),他是長子,特別斯文友善。兒童讀物那時候最有名的是東方出版社出的書,他家里有完整的西方古典文學、中國古典文學兒童再重寫版本,還有福爾摩斯等等。我就像突然有了一個圖書館,幾乎每周我都會點書,他帶來給我,看完我還給他,再換下一本。
那兩年是我很快樂的時光,我看了很多古典文學的童書版,很感謝那段時間。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基督山伯爵》和《茶花女》,對巴黎充滿了幻想。不過我最迷的是偵探類的小說,發(fā)現(xiàn)亞森羅平比福爾摩斯好看,因為我覺得他是反派的正義者,比較頑皮。
三明治:之前你被采訪時提過很早就看過瓊瑤的愛情小說,那是什么時候的事?
姚謙:應該是初中,以前在書店看過但看不懂,真的看明白是在初中。以前暑假我和我媽媽回娘家,鄉(xiāng)下有山有河嘛,我會玩得很瘋狂,我媽為了約束我,讓我必須睡午覺。我舅舅喜歡閱讀,家里有很多雜志和書,所以每天“午睡”一個小時,我就會讀舅舅的《皇冠》雜志上連載的瓊瑤小說。所以說我看瓊瑤中毒得很早,看完覺得,喔原來愛情是這個樣子,會經歷各種曲折,克服完之后才是偉大的愛情。
三明治:那個時候喜歡寫東西嗎?
姚謙:小學的時候我們有一個刊物叫《王子》,那時我已經在《王子》開始寫文章了,就是兒童雜志會讓兒童投稿,寫小學生作文,就像現(xiàn)在自己寫專欄一樣。雜志不會命題,會在投稿里進行篩選。
還有一個故事,到中學比賽考試,寫作文都是我的拿分項目。那時臺灣只有一家還是兩家電視臺,熱門動畫放完經常會出漫畫冊,電視臺就會征文,獲獎的人會免費得到漫畫冊,結果我真的就得到了,禮物一寄來就被父母當做珍藏本,那是整個臺灣的比賽。
三明治:寫作給你帶來許多獎勵,對于小時候的你或者爸爸媽媽來說,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吧?
姚謙:爸爸媽媽可能會覺得驕傲吧,對我來說,可能我天生不在意這些,就像我現(xiàn)在常常會覺得,“被人家認識”這件事不屬于我,即使現(xiàn)在工作需要面對很多人,我還是覺得,那是一個不屬于我應該面對的世界。這可能和我父親有關系,我父親到現(xiàn)在還是自己玩得很高興的人,我可能有遺傳到這樣的基因。我只有自己玩得很高興,我才能不被剝掉自由。

三明治:小時候有沒有想過,未來自己會和文字有這么深的關系?
姚謙:完全沒有。小時候被關注不是因為文字,我寫得好只是因為我愛寫、可以寫,但畫畫讓我被注意到,我還代表過我們城市去比賽。所以大一點的時候,我以為我的未來會和畫畫有關,我很喜歡美術,大學又學的是工業(yè)設計。不過后來美術不被看好,學校把美術科系關了,我們被迫轉系到紡織。當時不喜歡紡織,但現(xiàn)在我還挺喜歡服裝、布料,所以那時候挺挫折的。
三明治:但大學畢業(yè)之后,你的第一份工作和文字、畫畫都并不相關?
姚謙:畢業(yè)之后,傳統(tǒng)價值觀念里是要有穩(wěn)定工作,于是我就去一家汽車公司當展示員,穿很干凈的西裝,笑容可掬地向客戶介紹產品,想辦法把他的電話地址留下,讓業(yè)務員去銷售。雖然我不直接銷售,但展示員能留下多少電話,銷售人員才能有多少銷售可能,大家都有壓力。所以那時候生活不規(guī)律,腸胃就出問題了,我回家休養(yǎng)了半年。
身體實際上三個月就差不多養(yǎng)好了,另三個月沒有上班壓力,我就大量閱讀,去影像出租店租盜版電影,每天至少看一部,其他時間看書。那是我痛快閱讀的三個月,也能夠懂得思考一些比較深刻的問題。然后我就下定決心去徒步,從臺南越過中央山脈的南部橫貫公路,到達臺東。那是我第一次一個人旅行,一直在想人生到了25歲怎么辦這件事。
三明治:徒步歸來,對這個問題的思考有什么結果嗎?
姚謙:在徒步的過程中,我想我成為什么樣的人,和我做什么工作有關。我想進入的行業(yè)只有三個可能,出版社、電影、音樂,于是回來之后我就和家人說,并且開始寄履歷表給出版社、電影公司、唱片公司,我想先進去從最底層做起,哪怕是場務、美工、打雜的都行。后來我收到一些拒信,有的就根本沒回音,我去查怎么回事,才發(fā)現(xiàn)我投遞的職位全部在臺北,我的寄信地址在臺南,他們怎么會錄用一個身在臺南且沒有經驗的人呢?于是我決定去臺北,這樣至少能讓我的寄出地址是臺北的。
三明治:到了臺北之后,唱片公司的工作是你拿到的第一份錄用通知,還是你在幾家公司里選的?
姚謙:海麗唱片是第一個回復錄用我的公司,然后我就辭掉在臺北餐廳打工的工作去上班了。
三明治:所以這真的非常戲劇性,如果你拿到的第一份錄用通知來自電影公司或出版社,也許現(xiàn)在就不是音樂人了。
姚謙:對,如果第一份工作是在電影公司或出版社,我就在那里了。我現(xiàn)在慢慢理解自己,我是一個有計劃、有遠程目標的人,能一直耐著性子,直到得到我想要的。當時沒有選擇,三個行業(yè)里的任何一個都可以,我可以在一個行業(yè)熬十年。
“最懂女人心”的詞人?一個誤會
三明治:進入唱片公司之后,對未來有什么期待和規(guī)劃嗎?
姚謙:沒有特別的期待或者規(guī)劃,我一開始特別高興做這份工作。那時候唱片公司很小,不會覺得是可以賺到錢的工作,只是覺得很喜歡。當時有人說我是“笑面虎”,因為我上班老在笑,其實我是真的很開心,很享受那份工作。
三明治:最開始在唱片公司的工作內容是什么樣的?
姚謙:最開始樣樣都做,宣傳、公關都要做,后來唱片必須產業(yè)化,必須分工,我必須選擇面對媒體還是制作。我選擇了制作。我老板也覺得我更適合制作,因為我不喝酒,出去公關不合適,他覺得我過于樂觀,不夠復雜去盤算進退。有時候和媒體吃飯,沒話說了我就在那邊玩自己的或者看書,有一次最離譜,被灌了酒我也不知道拒絕,就在那邊睡覺。老板開玩笑說我是帶不出去的,所以我就做制作。
三明治:你進入唱片業(yè)之前,臺灣民謠火了一段時間了,有沒有自己嘗試著寫過歌詞?
姚謙:沒有,我對音樂是一直有興趣,我妹妹現(xiàn)在還是鋼琴老師,我也算是寫詞人里面少數能看譜看到很復雜譜子的人吧。但我知道我不是唱歌的人,我一直對唱歌、拿樂器表演是沒興趣的,我一直對上臺、名字被公開這種事,不是抵觸,而是希望保持不被刺激、保持無感的狀態(tài)。
我一開始在唱片公司寫文案,因為寫東西不錯。那時候唱片公司會從廣告公司挖角文案,所以很多寫詞人是廣告公司文案出身的,我是少數就是唱片公司出身的文案。當時老板找的寫詞人拖稿了,藝人又沒時間等,老板就問我文案寫了那么多,要不試試歌詞,我就連夜寫了。那是我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歌詞,也是我第一次意識到我有寫詞的能力,而且這個能力是被需要的。

三明治:號稱臺灣娛樂圈“教母”的張小燕曾經評價你是“最懂女人心”的寫詞人,很多人也都把你和“女人歌”聯(lián)系在一起,關于這個說法你認同嗎?
姚謙:這個最早是張小燕說的,那時候新聞標題就用“最懂女人心”,偏偏點擊率還很高。我不否認我對女性第一人稱的書寫還可以,但那次之后,大家好像都忘記我寫過男人歌,都只記得我寫女人歌,以前只是偶爾有人提起。
我覺得只是我的思維比較擅長對位思考,我現(xiàn)在看小說很多時候會以女一號的視角來看這個故事,比如最近的電視劇《我的前半生》,我很喜歡羅子君的媽媽這個角色,她的卑微、放大的自我保護,讓我很能體會。但最讓我沒感覺的是羅子君,完全是依賴男性塑造出來的角色,要靠一個無瑕疵的男人救贖,我特別反對。
三明治:你在臺灣的眷村長大,眷村應該是一個有很多故事的環(huán)境,這對你的寫作有影響嗎?
姚謙:我記得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覺,覺得北京就是放大很多倍的眷村。小時候家對面講長沙話,隔壁有山東口音,到北京了發(fā)現(xiàn)到哪都有口音,和眷村一模一樣,飲食也是有差異的,什么菜都有。
小時候印象最深刻的是,對面的周伯伯大概每周兩次左右會炒辣椒,他會通知大家關窗,避免被嗆到,尤其是小孩。所以每次家里要關窗我們就知道,周伯伯又要炒辣椒了。還有我們從小就知道山東饅頭最好吃,饅頭一定要買巷弄最里面那頭的山東伯伯家的。
眷村里大多是大陸軍人娶了臺灣本地女孩做太太,有各種各樣的口音,難免有沖突。有一天山東伯伯家吵架,她太太一直尖叫,很多人圍觀。那時候晚飯時間,家里不讓我們出門,我們吃完飯才被允許出去放風一下。我就很關心那家太太怎么樣了,偷偷去看。我現(xiàn)在說的時候還能想起來,我看到她還坐在那里哭,頭發(fā)被剪光了,圍觀的人都走了。她在坐在客廳偏走道的地方,我一直記得那個畫面,她半側著臉,頭發(fā)零零亂亂的樣子。
所以說我從小就是比較擅長換位思考,就像小時候只有20分鐘放風玩的時間,而我把那么寶貴的時間用來去看鄰居家的媽媽。
三明治:可以說你是天然地更關注女性主題,因為女性常是處于弱勢嗎?
姚謙:我理解你說的意思,但我覺得現(xiàn)在女性的地位是得到提高的,雖然很多女性還是很辛苦,特別是對未成年女性的保護和支持還是偏弱。我現(xiàn)在覺得“直男”這個群體反而是弱勢,特別是還沒有錢、沒有權、還在奮斗的直男,他們對取巧、柔韌不那么厲害,是非常脆弱的,所以我寫了《直男的脆弱》這篇文章。
還有最近的同婚(同性戀婚姻)制度,我發(fā)現(xiàn)當支持同婚慢慢變成主流,反同婚的人反而被嘲弄,被塑造成同一類的形象。我不反對同婚,我支持同婚,但我會覺得當反同婚的人都被指責,我會思考他們反對背后的原因,而不是一味說他們頑固、不了解世界、不體諒別人。當弱勢和強勢反過來了,對反同婚群體的呈現(xiàn)只有丑陋面,你愿不愿意去思考,他們是只有保守和食古不化而已嗎?所以我經常會和人爭執(zhí),同婚以前受壓迫,但現(xiàn)在成為主流時,反而會用同樣的方式對待曾經反對自己的人。
“我堅持每個字都是我選定的”
三明治:最近剛上市的新書《如果這可以是首歌》,是你的第六本書了,好像你的作品大部分是隨筆合集?
姚謙:我?guī)缀醵际请S筆合集,除了四年前的原創(chuàng)小說《腳趾上的星光》,其他都是用我在臺灣、大陸寫的很多專欄文章。出第一本書時,是之前一位唱片公司的員工去了一個出版社工作,他把我最早期在臺灣寫的專欄都翻出來,編好了來和我說,書名都起好了叫《我愿意》,我也不好說什么,就當幫年輕人創(chuàng)個業(yè)。專欄我很愿意寫,但如果不是第一本書他那么提,我是不會想出書的事的。當時我都不喜歡《我愿意》這個書名,但他們覺得這個名字符合商業(yè)訴求。
三明治:所以隨筆集基本上還是編輯整理出來的。
姚謙:所以也是承蒙看得起啊,我運氣比較好,有主編愿意幫我整理。像上一本《一個人收藏》是把以前書里沒有收的藝術類專欄整出來,這一本基本上集中最近三年的專欄,有一個比較主要的主題是旅行。這本書的編輯是我上一本書在西安簽售會的讀者,當時她還是大學生。和音樂一樣,我很想看年輕人的觀點,她的編輯我很喜歡。
三明治:最早是什么時候開始寫專欄?
姚謙:很早了,從最早臺灣報紙副刊有文學的時候我就寫了,比如《中國時報》、《文學時報》。那時候管理工作很多,所以沒有很固定地寫。后來發(fā)現(xiàn)大陸的文藝期刊文藝氣息很濃厚,我經常看,當他們有邀約的時候我就會寫,以前還是以女性月刊為主,近十年左右寫藝術類的更多。最近有一些新的變化是寫數位刊物(電子雜志),先期給訂閱用戶看,之后才能給公眾閱讀。
三明治:最開始寫的專欄是什么類型的作品?
姚謙:最開始我在點將唱片自己的刊物匿名發(fā)表短篇小說,那時候唱片公司都有自己的粉絲,會出專門給粉絲的刊物,我們的叫《點將錄》,一個月出1-2期。里面都是明星的資訊報道,唯一有一篇文藝小說,就是我的,每篇1000-1500字不等。那時候他們問我想寫什么,我說想寫小說,就寫了,用筆名發(fā)表,沒人知道是我寫的,現(xiàn)在我連筆名都不記得了。
三明治:如果自由寫作的話,似乎你更喜歡寫小說?
姚謙:其他隨筆專欄對我來說,像記日記,但小說是我到現(xiàn)在都念念不忘的,將來我還有寫小說的計劃。
三明治:可以聊一聊你六本作品里唯一的小說《腳趾上的星光》嗎?這個故事你用了書信體的方式來呈現(xiàn),是有什么特別的考慮嗎?
姚謙:我最早看的書信體小說,是一個意大利女作家的作品,故事講的是一個祖母給孫女寫信,那個孫女是祖母帶大的,叛逆期不讀書,獨居的老太太就開始和孫女寫信,寫到她過世,梳理一些女性關于家族、社會的經驗,很感人的一個小說。
《腳趾上的星光》講的是一對戀人在臺北和北京異地相愛,彼此通信。那個時候我剛剛開始從臺灣到北京工作,每個月一半時間在臺灣,一半時間在北京,生活有很多很大的變動。關于兩座城市生活的體驗,我有很多感悟想說,于是就把這些話化作一對情侶的書信對話,把那幾年的經歷濃縮到這對情侶的兩年里。
三明治:據說當時你為了寫這部小說,停掉了手上的很多工作?
姚謙:是的,當時停掉了手上很多事,采訪活動都不參加,朋友的活動也不參加,只寫作。小說里臺北部分的信我都在臺灣寫,北京部分的信全都在北京寫,我很看重書寫時現(xiàn)場即興的感受。平常我一般一個禮拜在北京,一個禮拜在臺北,但為了在北京完成北京部分的寫作,我特意把在北京停留的時間拉長到2、3個禮拜。那是2009年的冬天,后來再回頭看書里寫北京冬天的部分寫得特別生動,因為那時候我就生活在北京的冬天。我記得寫完之后就是2010年農歷過年,我回臺灣和家人過,后來花了差不多三個禮拜把后面臺灣部分寫完,潤稿花了一兩個月。
三明治:推掉所有工作寫小說,每天大概生活是什么樣的?
姚謙:《腳趾上的星光》這本小說寫之前,我是把故事大綱、結構全部提前想好、梳理好了,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按大綱寫完。每天寫作的時候我會安排好,起床后喝完咖啡,寫幾個小時,休息散步,再接著寫。晚上一定要抽離開,可能看個電影、聽會音樂,再睡覺。寫三、四天后我可能會休息一天。
三明治:比起寫小說,寫自己的專欄的時候,會不會比較隨性自由?
姚謙:以前工作時我是一個嚴格按時間表來做事的人,習慣了,書寫我也會找到自己的節(jié)奏。我剛剛在車上還在和工作人員說,問他們這幾天行程里,每天有哪幾個小時是有休息的,我知道我還有多少稿子、什么稿子要交,我會把時間很精準地分配完。
我一直說我希望自己“晚節(jié)能保”,我最大的“晚節(jié)”就是,我向來是個不拖稿的人,所有和我合作過的人都知道,我一般都會提前交稿,即使出去玩我都會是走在前面的那個人,因為我要知道下面的行程。
三明治:很多寫作者都是需要Deadline來催促他們完成任務。
姚謙:要催稿的是林夕不是我,哈哈。
三明治:剛才你提到手上會有很多專欄稿子要交,現(xiàn)在基本上每個月要寫多少篇?
姚謙:最多的時候我一個月要寫11篇,前陣子我把數量拉到每個月4、5篇,但最近又回到6、7篇一個月。
三明治:這是你2005年離開維京唱片,進入“半退休”狀態(tài)之后的情況嗎?
姚謙:是的,以前一個月3、4篇了不起了,這7、8年基本上都是每個月5篇以上。

三明治:寫作的時候,有沒有特別的寫作習慣?
姚謙:寫作的時候我希望要封閉空間,比如飛行的時候是一種更大的封閉,或者要么在家里,要么在酒店房間,手機一定是關掉。而且我一定要在書桌上寫,現(xiàn)在還是這樣。以前用手寫,現(xiàn)在是用手寫輸入法寫,手寫是讓自己不老化的方式之一,而且手寫是我選擇了這個字,我寫出來的就是我腦子里選的這個字,如果用其他輸入法,可能會跳出來更多、更漂亮的字,但它們都不是你選擇的那個,我還是堅持每個字都是我選定的。
三明治:無論之前寫歌詞還是寫專欄,文字工作量都很大,堅持手寫不會累并且影響效率嗎?
姚謙:有時候稿子有壓力會有點急,手寫比打字慢3、4倍吧,比如現(xiàn)在給別人上課的講義,一個禮拜兩期,要4000-6000字,手寫有我自己的節(jié)奏。我在iPad用手指寫,iPad寫完屏幕都磨舊了,不過手寫手指不累,累的還是腦子。以前沒電腦用手寫稿,幫我順第一次稿子的人最辛苦,經常要問這是什么字那是什么字,以前我會自己謄一輪,后來有助理會幫我確認交稿。現(xiàn)在輸入法也有聽寫功能,有時候可以聽寫。
三明治:那么寫歌詞的時候,有沒有什么特別的習慣,會等到靈感出現(xiàn)的時候再下筆嗎?
姚謙:不會,寫歌詞之前我必須聽熟曲子,定好主題,想明白整個結構,才會動筆。我現(xiàn)在在豆瓣的寫詞課上會反復說,寫歌詞一定要想好是什么結構再寫,然后再修改。
三明治:很多寫東西的人會有“完美主義”傾向,會覺得對自己的作品不滿意,反復修改,你會這樣嗎?
姚謙:我早就知道“完美主義”只是一種自我催眠。我不是說不追求更好,而是現(xiàn)在很多人用“完美主義”來包裝自己。“完美主義”的定義是什么?沒有一件事情有完美的標準,你可以更好,或者這個“好”在你計較的時候就消失了,在當下最好的時候抓住并記錄下來,才是智慧之舉。
三明治:你會隨身攜帶小本子抓住并記錄“最好的時候”嗎?
姚謙:有,現(xiàn)在包里還是會帶本子,有時間的時候會記錄會寫。
姚謙推薦閱讀的三本書
《未來簡史》
作者:尤瓦爾·赫拉利

我剛看完第二遍《未來簡史》,推薦大家思考它論述的邏輯。這本書在思考上有很多不成立的地方,但論述非常精彩,大家可以看它如何把論述寫得那么精彩。
《待月記》
作者:柳丹秋

我一直好奇二次元,終于有一本從二次元角度思考的小說,在國際文學比賽也拿了獎,駱以軍他們都在推薦,我看了一章覺得非常好,它是二次元第一人稱寫的,二次元大多是流于圖像,但這個時代新的二次元寫作還蠻稀有的,很有意思。
《觀看之道》
作者:約翰·伯格

英國人的書寫偏文學哲學,這本書關于藝術的閱讀,特別好,讓我們不再從美術史、歷史表象上去看,要從哲學、文學角度去讀美術作品。
三明治(公眾號ID:china30s)
轉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尾顯眼處標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載侵權必究。
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授權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必究。
本文禁止轉載,侵權必究。
授權事宜請至數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侵權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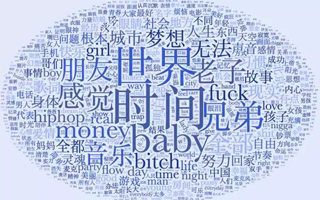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暫無評論哦,快來評論一下吧!
全部評論(0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