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色一生》:日本97歲奶奶用染織書(shū)寫(xiě)人生,被封人間國(guó)寶

自述:志村福美,志村昌司,撰文:余璇 ,責(zé)編:石鳴 ,來(lái)源:一條
原標(biāo)題:97歲奶奶絕色一生,被封人間國(guó)寶
2021年1月,《一色一生》一出版就刷了屏,豆瓣評(píng)分高達(dá)9.2,讀過(guò)的人驚艷于這本書(shū)“破格的美”,更打動(dòng)人的是作者志村福美傳奇而勵(lì)志的一生:
三十二歲,離婚帶兩個(gè)小孩,為了謀生開(kāi)始做染織,四十歲,舉辦第一次作品展,六十六歲,被認(rèn)定為日本“人間國(guó)寶”,九十歲,獲有“日本諾貝爾獎(jiǎng)”之稱(chēng)的京都獎(jiǎng),川端康成評(píng)價(jià)她的作品:“優(yōu)雅而微妙的配色里,貫通著一顆對(duì)自然謙遜而坦誠(chéng)的心。”

用植物染的各色絲線織成的裂
《一色一生》是志村福美58歲時(shí)寫(xiě)的書(shū),書(shū)里回顧了她的前半生,以及她對(duì)植物、自然和生命的種種思考。將近四十年后,此書(shū)終于被譯介到中國(guó),我們也借此機(jī)會(huì)獨(dú)家專(zhuān)訪了已經(jīng)97歲高齡的志村福美奶奶,以及她的女兒和外孫,拜訪了她創(chuàng)立于京都的工坊和藝術(shù)學(xué)校,“九百年來(lái),我們一直在用同樣的方法染色,染線、紡線、織布,做成衣服,用這樣的衣服裝飾自己,和買(mǎi)來(lái)的衣服比,懷有的情感是很不一樣的吧。”
志村福美:為染一色,付出一生

《一色一生》是日本染織家志村福美的自傳性隨筆集,1982年出版后,第二年便獲得了大佛次郎獎(jiǎng)(日本最高文學(xué)獎(jiǎng)之一)。從那時(shí)到現(xiàn)在,這本10萬(wàn)余字的小書(shū)已在日本暢銷(xiāo)了30余年。
書(shū)中記錄了她如何用不同植物的根、莖、花、果、枝做成染液,如何做藍(lán)染,如何織布,以及她從染織這件事中收獲的種種思考,關(guān)乎顏色、植物、自然和生命。比如:“色彩不只是單純的顏色,它是草木的精魂。”“蘇芳是女人內(nèi)心的顏色,被喻為紅淚。在這赤紅的世界里,住著圣女,也住著娼婦,她們同樣擁有女人的深情。”文字優(yōu)美,富有詩(shī)意。




由上及下分別是:《櫻花襲》1976年,《梔子熨斗目》1970年,《勾蘭》1987年,《松風(fēng)》2003年,皆為志村福美創(chuàng)作,分別由個(gè)人和滋賀縣立近代美術(shù)館收藏
志村福美曾與一批日本民藝大師相交、相知,柳宗悅、富本憲吉、河井寬次郎、稻垣稔次郎等都曾給她引導(dǎo)。她也深受歌德《色彩論》、斯坦納《色彩的本質(zhì)》和蒙德里安作品的啟發(fā)。盡管是人到中年才投身染織,志村福美卻憑借極強(qiáng)的色彩天賦和動(dòng)手實(shí)驗(yàn)的精神,積極地投入創(chuàng)作中。
她用日本民間最常見(jiàn)的“?織”①做出的小裂(布片),色彩微妙,難以模仿:藍(lán)黃交錯(cuò)的,如天空和大地的呼應(yīng),黑白混織的,像被白雪覆蓋的村莊,橫格紋、米字紋、平行線……不只是紋樣,更像是一幅幅奇妙的畫(huà)作。

志村福美在2014年京都獎(jiǎng)?lì)C獎(jiǎng)典禮上
在日本工藝界和文學(xué)界,志村福美的成就早已得到公認(rèn)。早在1990年,她就被授予“人間國(guó)寶”稱(chēng)號(hào)。2014年,她獲得了有“日本諾貝爾獎(jiǎng)”之稱(chēng)的京都獎(jiǎng),頒獎(jiǎng)詞是:“在化學(xué)染料興盛的當(dāng)下,堅(jiān)持用植物染色的絲線作為自己的視覺(jué)語(yǔ)言,然后再織出千變?nèi)f化的作品,將人與自然在紡織中融合在一起。”2015年,她又被授予“文化勛章”,獲日本國(guó)家最高榮譽(yù)。
她還開(kāi)設(shè)了藝術(shù)學(xué)校“Arts Shimura”,致力于推廣染織技藝。在這里,學(xué)員們可以自己染、自己織、自己裁剪制衣,許多人感慨:把這樣純手工做出來(lái)的衣服穿在身上,那種體驗(yàn)和買(mǎi)來(lái)的衣物完全不同!今年1月,《一色一生》的中文版歷經(jīng)五年周折,終于翻譯出版。借由這個(gè)契機(jī),我們連線了97歲高齡的志村奶奶。由于疫情,志村奶奶目前住在京都近郊的療養(yǎng)院里。透過(guò)視頻,我們看到消瘦、蒼老的她,白發(fā)如雪,唯獨(dú)神情中透露出的堅(jiān)毅和年輕時(shí)有幾分相似。
她對(duì)我們說(shuō),“一色”絕非只限于她畢生躬親的藍(lán)染,“每一種顏色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都是一生中珍視的寶物”。
以下是志村福美的自述:
一、半路出家做染織

年輕時(shí)的志村福美
32歲的時(shí)候,我離了婚,帶著兩個(gè)孩子,不知道怎么辦才好。當(dāng)時(shí)正好和民藝創(chuàng)始者柳宗悅交流,他對(duì)我說(shuō):“你母親會(huì)紡織,你也去織布吧。”于是我決定回到近江,以染織為生。這個(gè)決定遭到了母親的堅(jiān)決反對(duì)。當(dāng)時(shí)正是化學(xué)染料興盛的時(shí)期,草木染、手工織物,代表著貧乏、落后、瀕臨滅絕。她塞過(guò)來(lái)一張回東京的車(chē)票,并要我再也別回來(lái)。我一度絕望地離開(kāi),但就像是被一根無(wú)形的線牽引,又再度返回母親身邊。



用植物染的絲線織成的裂
正式投入之后,我沉迷其中,在我眼前展現(xiàn)出的,是用盡一生也做不到的精彩世界。我就像是漫游奇境的愛(ài)麗絲跌進(jìn)兔子洞那樣,窺探到一個(gè)神奇的國(guó)度:早春時(shí)節(jié)的梅枝,可以染出的珊瑚色,宛如少女臉頰上的一抹腮紅。 藍(lán)染的甕伺、水淺蔥、紺等不同程度的藍(lán),如同海洋與天空。初冬時(shí)節(jié),熬煮熟透的梔子果,得到溫暖而耀眼的金黃色。還有用蘇芳染成的赤紅色,云霞一般美麗的櫻色,等等。

當(dāng)初我窮得連一塊桌布也買(mǎi)不起,只能把孩子放在東京的養(yǎng)父母家中,在近江的染坊和織坊里學(xué)習(xí)基本功。我想要有收入,至少能買(mǎi)得起絲線,也想盡早把孩子接到身邊。
母親建議我去拜訪一位木工——黑田辰秋,她說(shuō),黑田先生是一個(gè)無(wú)論忍受何種貧窮,都不會(huì)在工作上妥協(xié)的人。“工作有時(shí)像是地獄,生活很辛苦,所以我無(wú)法勸你走這條路。但如果你認(rèn)定自己別無(wú)選擇,那就做下去。首先織出自己想穿的衣服,將來(lái)可以暫且不去考慮,只是專(zhuān)注于眼前的工作。”黑田先生對(duì)我說(shuō)。
聽(tīng)了這樣的話(huà),我下定決心,無(wú)論如何也要朝著這條路走下去。女人守在丈夫和孩子身邊,燒飯、洗衣、做家務(wù)似乎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對(duì)于隨波逐流,平穩(wěn)安逸地生活下去的女人本身,如今我會(huì)用另一種眼光去看待。我必須逆流而上,一個(gè)人奮力劃行。
二、母親說(shuō): 你再不會(huì)做出比這更好的作品了

志村福美作品:《方形紋綴帶》局部,1957年
我的第一件作品是在黑石先生的鼓勵(lì)下做出來(lái)的《方形紋綴帶》,入選第四屆日本傳統(tǒng)工藝展。
那天晚上,我悄悄從母親的籃子里取出了絲線,織了一條腰帶。我近乎忘我地織,等到腰帶完成,已經(jīng)是第二天的清晨。當(dāng)時(shí)臥病在床的母親看到那條腰帶,高興地說(shuō):“做到這一步,就算落選也值得。你盡力了。”

《秋霞》,志村福美的代表作,獲第五屆日本傳統(tǒng)工藝展獎(jiǎng)勵(lì)獎(jiǎng)
我的第一件獲獎(jiǎng)作品是和服《秋霞》。這件和服是將普通農(nóng)婦家用剩下的線連在一起織成的。在過(guò)去,日本農(nóng)婦會(huì)將用剩的線接在一起,叫作“績(jī)線”。這件和服雖然低調(diào)樸素,但是我覺(jué)得很有現(xiàn)代的味道,綠色、藍(lán)色、紺色,中間還夾雜著白色絲線。剛做好的時(shí)候,我把它拿給母親看,她說(shuō):“你再不會(huì)做出比這更好的了。”果然是這樣。
現(xiàn)在回頭看,《秋霞》以外沒(méi)有能超越其上的了。 在此之后,我又創(chuàng)作了《鈴蟲(chóng)》《七夕》《霧》《待月》等系列作品。坐在織機(jī)前投梭引緯,不經(jīng)意會(huì)有彈撥豎琴的心境。經(jīng)線奠定了某種基調(diào),紗線則是可以即興發(fā)揮的部分,如果能找到合適的顏色,絲線就會(huì)像被吸進(jìn)去一樣,啪嗒一下穩(wěn)穩(wěn)地融入織紋中,這就是?織的魅力。



《鈴蟲(chóng)》1959年、《七夕》1960年、《蘆刈》1961年,志村福美作品,滋賀縣立美術(shù)館藏
1982年的某一天,我接到了一個(gè)陌生電話(huà),電話(huà)另一端“報(bào)告”說(shuō),自己屋前的一顆老榿[qī]樹(shù)被伐倒了,木屑灑在地上,將土地染得通紅,像是從樹(shù)中淌出的鮮血,問(wèn)我是否可以用來(lái)染布。
掛了電話(huà),我立刻備車(chē)出門(mén)。趕到現(xiàn)場(chǎng)后,看到巨大的樹(shù)樁四周,土地已經(jīng)被染成了茶紅色,那是上百歲的古榿木中儲(chǔ)存的汁液染成的。我立即認(rèn)定這是可以用來(lái)制作染料的木材,于是絲毫不敢耽擱,匆匆剝下樹(shù)皮裝入袋中,下山去了。
支起大鍋,熬煮樹(shù)皮,鍋中的液體在加熱的過(guò)程中轉(zhuǎn)為透明的金茶色。然后將絲線放入過(guò)濾后的染液中反復(fù)浸染,最后用木灰水固色,絲線就變成了赤銅色。那是榿木的精魂之色。我恍惚感到榿木復(fù)活了。

志村福美家鄉(xiāng)的琵琶湖雪景(左),《湖北雪景》之裂(右)
后來(lái)我在《一色一生》中記下了這個(gè)故事,我想說(shuō),從這些植物中獲得的,已不是單純的顏色,蘊(yùn)于其背后的植物的生命,正通過(guò)色彩顯露于我。那是植物用自己的身體在傾訴。所以在取色的時(shí)候,我們一定要尊重植物,珍惜植物。
三、做植物染色,就像把孩子漸漸養(yǎng)大一樣
如今回想起來(lái),我對(duì)植物染色的感受和體會(huì)強(qiáng)于織作。從工藝的角度看,獲取優(yōu)質(zhì)的材料是第一要義,是根基。
剛開(kāi)始做染織的時(shí)候,我曾把自己用化學(xué)染色的絲線和母親植物染的絲線掛在一起,相比之下,母親十幾年前染的絲線柔和、光亮,富有生命力,而自己的絲線則呆板鈍澀。后來(lái)染色工藝家芹澤????介提醒我說(shuō):“將植物染的織物丟到原野上,兩者會(huì)融為一體。”從那之后,我決心只做植物染。


說(shuō)到植物,我們以為綠色是最容易染出的,但不可思議的是,并沒(méi)有單獨(dú)的綠色染料,它需要由黃與藍(lán)混合才能得到。黃色用黃檗、青茅、梔子、福木等染成,然后用藍(lán)調(diào)和,就會(huì)得到綠色。
我也曾試著將大紅色的薔薇花瓣倒入大鍋中做染液。一加熱,花瓣立刻流出濃濃的胭脂色汁液,接著轉(zhuǎn)為淡紅。我以為可以染成,結(jié)果染出來(lái)的顏色并無(wú)紅意。色彩的真相就像是一個(gè)寓言,道出“色即是空”的本義。
我曾有幸得到深見(jiàn)重助在明治三十四年(1901)染的茜色絲線。第一眼我就被那色彩吸引了。恍惚間它已不是一束線,而是一卷經(jīng)文。這束線是紅色中略帶黃調(diào),近似于燃燒的火焰。這種深茜染,染一貫線要用一百貫茜根,耗時(shí)一年半,然后要在染料和木灰水中交替浸染一百七十次才能染成,如果在第一百六十九次失手,就前功盡棄。所以染色就像是修行,就像柳宗悅老師說(shuō)的:“染色,就是染心。”


《水琉璃》為東京國(guó)立近代美術(shù)館藏記憶中,母親總愛(ài)穿藍(lán)染的衣服。“再?zèng)]有比藍(lán)染更適合日本女性的裝扮了!”這是母親常說(shuō)的話(huà)。藍(lán)草與其他植物染料有著根本區(qū)別。幾乎所有的植物都是用熬煮之后的染液進(jìn)行染色,唯有藍(lán)染,我們需要從專(zhuān)業(yè)的藍(lán)師那里獲取藍(lán)靛,然后與麥麩水一起發(fā)酵而成。
藍(lán)染是人類(lèi)使用時(shí)間最長(zhǎng),也最復(fù)雜的一種植物染。在日本,藍(lán)染分為建藍(lán)、守甕和染色三個(gè)步驟。搬到嵯峨以后,我的建藍(lán)之夢(mèng)得以付諸實(shí)踐。我牢記 “做藍(lán)染就像養(yǎng)育孩子”的教導(dǎo),努力堅(jiān)守并培育藍(lán)的生命。每一只染甕里都蘊(yùn)藏著藍(lán)的一生,且每天都在微妙地變化。


藍(lán)染染缸和藍(lán)色絲線
早晨揭開(kāi)染甕的蓋子,染液正中開(kāi)著一朵由暗紫色泡泡匯聚而成的靛花(或叫藍(lán)之顏)。觀其色澤,可以察知藍(lán)的心情。待熾烈的藍(lán)氣發(fā)散,藍(lán)的青春期可以讓純白的絲線在一瞬間閃耀翠玉色的光輝,又迅疾地變幻為縹色;在經(jīng)歷了沉穩(wěn)的琉璃紺的壯年后,藍(lán)色成分漸漸消隱,當(dāng)絲線被染成如水洗過(guò)的水淺蔥色,就是業(yè)已老去的藍(lán)之精魂。
過(guò)了很久我才知道,這種顏色叫作“甕伺”。所謂甕伺,指染甕里帶著一點(diǎn)淡淡水色,那是藍(lán)晚年最后的顏色。

藍(lán)染中的天然藍(lán),以及木灰水里,都會(huì)摻雜一些雜質(zhì),因此藍(lán)染不會(huì)像人造藍(lán)那樣濃艷。藍(lán)染會(huì)染出的各種深淺濃淡的藍(lán),凝視他們,仿佛自然界的法門(mén)兀自開(kāi)啟,各種音色在耳邊喧響。記得陶藝家富本憲吉在陶瓷上作畫(huà)時(shí),也喜歡用下等的天然染料,越是不純凈的染料,燒出來(lái)的藍(lán),就越會(huì)有不同的變化,帶有一種厚重的韻味。
有趣的是,在藍(lán)染的工坊作業(yè)時(shí),工匠們會(huì)身著白色的服裝,據(jù)說(shuō)是為了提醒自己要?jiǎng)幼鞒练€(wěn),心態(tài)平和。
四、染織,是我的命運(yùn)

18歲的志村福美
我在兩歲時(shí)與母親分離,在叔父家當(dāng)了十多年的養(yǎng)女。因此我管親生父母喊伯父伯母。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里,這件事及其帶來(lái)的影響,都在我對(duì)母親的感情中投下了復(fù)雜陰影,但如今想來(lái),一切都是命運(yùn)使然。
上女子高中二年級(jí)的夏天,我第一次獨(dú)自從東京回到近江,“伯父”是醫(yī)生,家里不時(shí)有訪客出入,我與“伯母”幾乎沒(méi)有碰面的機(jī)會(huì)。過(guò)了一會(huì)兒,她突然走到我面前,放下了幾本梵高畫(huà)集,又慌忙退回到里間。那時(shí)候我隱隱意識(shí)到有一種骨肉之親的聯(lián)系。兩年后,二哥病重,我再次返回故鄉(xiāng),與父母兄妹相認(rèn)。我們圍著暖桌而坐,開(kāi)誠(chéng)布公地暢聊了一整晚。母親說(shuō)起當(dāng)時(shí)她把我送走的時(shí)候,是下定決心當(dāng)我不在人世的。她沒(méi)有想到自己送走的女兒竟然會(huì)回來(lái)相認(rèn)。
在家中陰暗的雜物間,一臺(tái)織機(jī)引起了我的注意,我追著母親問(wèn)了好多問(wèn)題,后來(lái)她為我組裝起織機(jī),繃上了藍(lán)染絲線。這或許是一種奇妙的緣分,我與母親相認(rèn)的同時(shí),遇到了織機(jī)。


《蘇芳段暈染》為東京國(guó)立近代美術(shù)館藏
我的母親小野豐和柳宗悅相識(shí),我也非常尊敬他。在日本,柳宗悅的佛教美學(xué)思想影響很深,我的工作中也融入了一些柳宗悅佛教美學(xué)的思想。比如:“染色就是染心,織作,需要去了解事物的真實(shí)狀態(tài)。”這都是柳先生教我的最根本的東西。離開(kāi)東京投身染織的前一天,我去拜訪了富本一枝女士,富本憲吉先生的夫人,她是母親的朋友,也是名藝術(shù)家。三十多年來(lái),她被夾在事業(yè)和家庭之間,也有過(guò)很多苦惱。
她對(duì)我說(shuō):“女人是活在家庭中還是活在事業(yè)上,這兩條路不可能兼得。要認(rèn)準(zhǔn)一項(xiàng),全心全意地投入。現(xiàn)在的日本,對(duì)于擁有事業(yè)的女人依然抵觸強(qiáng)烈。但是這幾十年來(lái), 我見(jiàn)過(guò)不少活在事業(yè)上的女性。這些人中,有的一度舍棄了家庭,最后因事業(yè)有成又破鏡重圓。總之要徹底。半調(diào)子是一種罪過(guò), 對(duì)丈夫、孩子和自己都是不幸。義無(wú)反顧地做下去吧。”
那時(shí), 我正為失眠和低落懊惱的情緒所困, 在一片黑暗之中彷徨, 舍棄家庭仍讓我于心不忍。但一枝女士的一番話(huà), 把我的煩惱干脆利落地剔除干凈。在荒草叢生的前方, 我仿佛看到了一條路。


每當(dāng)我創(chuàng)作受阻,都會(huì)去找稻垣稔次郎先生(染織家)。先生極少點(diǎn)評(píng)我的作品,卻會(huì)鼓勵(lì)我:“塞尚一路潛心研求,最后抵達(dá)的是自然。自然擁有神奇的力量,抓住其本來(lái)面貌,準(zhǔn)確無(wú)誤地表達(dá)其中的真理,這是工作的真正根基。”
我曾以《秋霞》為題做了一件繪羽風(fēng)格的?織和服。有位老師對(duì)我說(shuō),不以用為第一要義的?織,是不被承認(rèn)的。當(dāng)時(shí),?織和服普遍用作日常便裝,像我這樣織成一整幅畫(huà)的幾乎沒(méi)有。我對(duì)自己的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疑問(wèn)。后來(lái)稻垣稔次郎先生的一語(yǔ)驚醒夢(mèng)中人:“做出一件衣裳,不是給現(xiàn)實(shí)中的女性,而是給幻想中的女性穿,不是也很好么?”
從那以后,我也決心要做和服,給幻想中的女性穿。

念小學(xué)一年級(jí)的志村福美
我小時(shí)候在中國(guó)住過(guò)一段時(shí)間,也去過(guò)上海,在那里有各種各樣的回憶。中國(guó)文化是日本文化的起源,佛教也是從中國(guó)傳過(guò)來(lái)的,所以我對(duì)中國(guó)非常尊重。我覺(jué)得中國(guó)藝術(shù)最厲害的是書(shū)法。顏真卿、王羲之這些人在我看來(lái)非常了不起。不管是西洋的藝術(shù)還是中國(guó)的藝術(shù),我都會(huì)被吸引,而最讓我驚訝的,是植物的美。它是大自然的饋贈(zèng),不是我們花心思調(diào)配就可以獲得的。
曾經(jīng),我以為做一色會(huì)耗費(fèi)十年;如今,我覺(jué)得做一色將用盡一生。
五、已經(jīng)到了重新思考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的時(shí)代
以下是志村昌司(外孫)的自述:
雖然我的外婆、媽媽都是從事染織的,但是我一開(kāi)始并不感興趣,大學(xué)學(xué)的也是哲學(xué)專(zhuān)業(yè)。

志村福美在工坊的織機(jī)前,攝影:Alessandra Maria Bonanotte
2011年的時(shí)候,發(fā)生了東日本大地震,整個(gè)日本陷入社會(huì)危機(jī)。尤其是福島核電站泄漏事故,影響很大。聽(tīng)在東北從事草木染工作的人說(shuō),如果有核泄露,就不能再?gòu)氖逻@項(xiàng)工作了。我就覺(jué)得到了重新思考人與自然之間關(guān)系的時(shí)代了。從那時(shí)開(kāi)始,我就加入了染色的工作。染織這項(xiàng)傳統(tǒng)工藝,是從平安時(shí)代一直流傳下來(lái)的。制作方法也是,大約八九百年前就一直用同樣的方法進(jìn)行染色,從這個(gè)意義上講,日本的染織工藝是沒(méi)有中斷的。
在我們家,分染色、紡織兩步。首先是用植物染色。現(xiàn)在是春天,我們會(huì)用梅樹(shù)枝、櫻花樹(shù)枝之類(lèi)的染色。染完后會(huì)將染好的絲線保存起來(lái),一次不會(huì)全部用完。外婆有時(shí)候都舍不得用那些漂亮的絲線。接下來(lái)就是加工紡織,一般需要兩三個(gè)月的時(shí)間。清早開(kāi)始,到晚上五六點(diǎn)結(jié)束,就這樣度過(guò)一整天。

織機(jī)上的經(jīng)線
外婆最?lèi)?ài)的藍(lán)染,是從我孩童時(shí)代就有的記憶。藍(lán)靛和其他植物染料不一樣,它是養(yǎng)育出來(lái)的。櫻染、梅染,都是取樹(shù)枝煮成染液,然后去染色。藍(lán)染則需要發(fā)酵、發(fā)泡,放置兩三周的時(shí)間再染色。我們從新月著手準(zhǔn)備,到滿(mǎn)月開(kāi)始染色,這與宇宙的運(yùn)行步調(diào)是一致的。
母親和外婆都非常重視藍(lán)染。每一次染色,我們都會(huì)很感動(dòng)。但外婆對(duì)我影響最大的,是思考方式。她是在柳宗悅的影響下開(kāi)始染色的。我覺(jué)得柳宗悅民藝思想中最重要的一點(diǎn),就是從日常生活中發(fā)掘美的思考方式。因此我們?cè)谑止ぶ谱髦校瑢W(xué)習(xí)美的生活方式,思考人與自然的關(guān)系,也很重要。

染完了就要織布。織布并不難,只是很費(fèi)時(shí)間。一個(gè)普通的紋樣,會(huì)需要織幾個(gè)月。具體花多久時(shí)間,還是要看它的設(shè)計(jì)。順便說(shuō)一下,在織機(jī)上,經(jīng)線有一千兩百支,緯線大概要織四萬(wàn)次,這樣“砰砰”地將梭子穿來(lái)穿去,然后“打”著做。如果將織布視為工作去做,會(huì)覺(jué)得很辛苦,但如果看作自己的興趣,就會(huì)在紡織的過(guò)程中感受到快樂(lè)。手工藝不就是享受制作的過(guò)程么。
外婆后來(lái)開(kāi)設(shè)了藝術(shù)學(xué)校“Arts Shimura”。在這里,學(xué)員們可以自己染、自己織,從一開(kāi)始到最后,都是手工完成。把這樣做出來(lái)的衣服裹在身上,那種感受和買(mǎi)一件衣服完全不同。


《紫紺格子》為滋賀縣立近代美術(shù)館藏
我們面對(duì)的當(dāng)下,是一個(gè)追求效率化的時(shí)代,而手工藝會(huì)花費(fèi)特別多的時(shí)間,如何保持自信?能留下些什么?我想這是外婆生活的時(shí)代里沒(méi)有的課題。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傳統(tǒng)工藝運(yùn)用到教育中,讓更多的人了解這件事。
注:
①:?(chóu)織”,日語(yǔ)詞匯,把用手捻成的絲線,以橫豎相交的方式進(jìn)行紡織。
部分資料來(lái)自志村福美的著作:
《一色一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月版
《奏響色彩》,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
《我的小裂帖》,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
特別感謝:
志村工作室(atelier shimura)
拙考文化
題圖攝影:敏子同學(xué)
作者公眾號(hào):一條(ID:yitiaotv)
轉(zhuǎn)載請(qǐng)?jiān)谖恼麻_(kāi)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qǐng)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hào)(ID: digitaling) 后臺(tái)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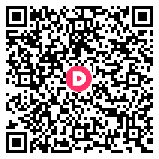

評(píng)論
評(píng)論
推薦評(píng)論
全部評(píng)論(5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