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章程,首發(fā):一點(diǎn)兒烏干菜
我把寫李誕的文章《當(dāng)我們談?wù)摾钫Q時我們談?wù)撌裁础贩旁诙拱辏瑳]想到引起了熱議。一個讀者拋給我一個問題:在資本為王成長起來的90后,在接受著“讀書就能改變命運(yùn)”成長起來的90后,遇到的是什么?是在資本浪潮中個人力量的渺小,是試圖通過自己改變命運(yùn)卻不如一個好爹的無奈,是階級逐漸固化后,年輕人的那種無力感。如何消解這種無力感,如何與社會和解?
這個問題太龐大了,我當(dāng)時給她的回復(fù)是:你說的這個問題,是否在每一代身上都會遇到。80后有80后需要面對的現(xiàn)實(shí),90后有90后需要面對的現(xiàn)實(shí),每一代終將遇到理想與現(xiàn)實(shí)的鴻溝。只是,我們所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shí)是消費(fèi)社會愈來愈強(qiáng)大,我們這代人的境遇多少類似于日本當(dāng)下“低欲望”社會,日本青年人也變得“佛系”,雖然他們沒有這個詞。至于去應(yīng)對這種現(xiàn)實(shí)的策略,我暫時還沒有想好。不過我相信熊培云的話,年輕時候要是還沒想好干什么,或是不確定自己適合干什么,要么努力賺錢,要么多讀點(diǎn)書,想要讓自己更自由,這二者必不可少。
可是,我始終覺得關(guān)于這個問題闡之未盡。周末看了《三塊廣告牌》,覺得這片子和《海邊的曼徹斯特》一樣喪,所有人的人生似乎都是破碎的,每個人都疲于應(yīng)對著生活。在整個壓抑的電影氛圍中,弗蘭西斯·麥克多蒙的炸裂的演技卻提醒了我:哦,原來你可以喪,但卻可以牛逼哄哄的喪著。

▽
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在電影中飾演的一位脾氣暴戾,性格強(qiáng)勢且獨(dú)立的女性,她的生活確實(shí)夠“喪”,她的丈夫離開了她,和一個十九歲的姑娘同居,她的女兒因?yàn)榕c她爭執(zhí)離家后被強(qiáng)奸殺害,她租用了三塊廣告牌矛頭直指警察的不作為,這個罹患癌癥廣受鎮(zhèn)上人民愛戴的警察局長因此不堪重負(fù)而自殺,所有人都批評她的冷漠。除了自己的兒子與好友,她儼然已經(jīng)已經(jīng)成了鎮(zhèn)上人們的公敵。似乎她生活的一切都乏善可陳,仿若美國版的《被嫌棄的松子的一生》。

為了泄憤她燒毀了警察局,她對前來疏導(dǎo)她的牧師惡語相向,甚至對給她車窗丟雞蛋的學(xué)生她也絲毫不留情面。她為了自己的一個信念和整個世界為敵。

影片中我最喜歡結(jié)局,她向洛克威爾飾演的那個吊兒郎當(dāng)?shù)木焯拱祝骸坝屑挛腋阏f,警察局的火是我放的。”“我知道,除了你還能是誰。”洛克威爾漫不經(jīng)心地應(yīng)聲道。那一刻,她會意一笑,這似乎是她在全片唯一的一次笑容。兩個人在那一瞬間已經(jīng)完全和這個世界和解了吧。與其說去復(fù)仇,反倒像是自我救贖之旅。

我不覺得她最后的和解,只是在那一個契機(jī)下突然對生活溫柔以待了,她此前的西緒弗斯式的抗?fàn)幍拇鷥r,才換來了最后與自己和解的“自由”。讓自己更自由從來都不是件容易的事,沒有一種人生是夠輕松的。科恩有句話現(xiàn)在被廣為流傳:“萬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進(jìn)來的地方。”所謂的成熟,成長的代價就是這樣吧,把自己的內(nèi)心揉皺,甚至撕裂,最后還是要把它熨妥帖,放平整。

牛逼哄哄的喪著,只是提醒著你,你不能就這么輕易地對生活的“喪”姑息的。
▽
17年看《至暗時刻》,看哭了,與我類似的還有一個同學(xué),有人就在問:“很好奇你們直男的淚點(diǎn)在哪里?”大抵,最能觸動自己內(nèi)心最柔軟處的,無非是那種明知不可而為的決絕,那種永不姑息和妥協(xié)的傲慢。

所以,與《至暗時刻》講述同一個現(xiàn)實(shí)卻用另一個角度敘述的《敦刻爾克》也觸到了我內(nèi)心。《敦刻爾克》中軍人們被民眾自發(fā)組織的漁船陸陸續(xù)續(xù)送回來了,他們原本擔(dān)心自己只是作為一個失敗者回歸,甚至為此羞赧。可是家鄉(xiāng)的人們卻向迎接勝利者一般迎接著他們,車窗外的人們歡呼著,給他們啤酒和面包。此時,丘吉爾的那段著名演講在背景中響起:
“我們將在法國作戰(zhàn),在海上作戰(zhàn),乘著高漲的信心和力量空中作戰(zhàn),不惜一切保衛(wèi)我們的家園。我們將在海灘作戰(zhàn),我們將在敵軍登陸點(diǎn)作戰(zhàn),在平原和街巷作戰(zhàn),在山野作戰(zhàn)。我們永遠(yuǎn)不會投降。”

這大概是我能想見的人類歷史最偉大的時刻,那個固執(zhí)又倔強(qiáng)的老頭丘吉爾憑著廣播鼓舞著即將失去抵抗抵抗信念的國民的士氣。
喪文化的流行雖然是當(dāng)下時代的一個特征。可其實(shí),所謂的喪,無非只是一種生存的狀態(tài)。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喪。只是湊巧,我們這一代碰到了互聯(lián)網(wǎng)的空前壯大,所以我們的抱怨,自怨自艾,可以被網(wǎng)絡(luò)這個媒介放大,傳遞。丘吉爾的時代有丘吉爾時代的喪,納粹以狂飆突進(jìn)之勢席卷著歐洲,英國的軍隊接連敗退,在敦刻爾克四面楚歌,絕望無助。我不覺得英國軍隊所面對的這個整個民族即將如喪家之犬的態(tài)勢會比我們當(dāng)下現(xiàn)實(shí)更輕易,更容易承受。這段歷史太過沉重,以至于在《敦刻爾克》中,諾蘭根本不需要在電影中放過多的臺詞,因?yàn)楝F(xiàn)實(shí)只剩下喑啞和嗚咽。

即便我們反觀丘吉爾,現(xiàn)實(shí)中的丘吉爾,身材肥胖,酗酒抽煙,常常言辭不清讓人以為是囈語,而且他終其一生都在和如夢靨般隨行的抑郁癥抗?fàn)帲诤湍莻€酗酒的父親的原生家庭所帶給他的焦慮和壓抑抗?fàn)帲桓宜陉柵_上,原因是那種想一躍而下的沖動隨時會有。

每一個金燦燦的人生和歷史時刻,撕開光鮮后,似乎都是那么普通,甚至殘酷。“喪”并不是你拒絕外界,對現(xiàn)實(shí)放棄抵抗的擋箭牌。
▽
楊絳先生有一句話特別適合用來解釋“喪文化”:你的問題主要在于讀書不多而想得太多。
14年的時候《馬男波杰克》一度成為了這種“喪文化”的標(biāo)志,每次見到有人在分享《馬男波杰克》里面的金句,這些如“葛優(yōu)癱”一樣風(fēng)靡的喪氣滿滿的話,似乎都有一個不滿現(xiàn)實(shí)的年輕人隱藏在這些言語的背后哀嘆自艾,失意遣懷,把“喪”作為深諳與洞悉世事和人性后的抉擇。

《馬男杰波特》里,提供了兩種人格的原型,一種是“Zelda”型的,外向樂觀,溫暖善良,他們是聚會上的焦點(diǎn),以花生醬先生為代表,一種是“Zoe”型的,尖酸刻薄,自私自欺,又自戀自大,以馬男為代表。

幾乎每個人的人格里總是這兩種類型在此消彼長地較量著,當(dāng)我們無限接近于后者,也就靠近了所謂的“喪文化”。“喪文化”下的年輕一代對奮斗、消費(fèi)、買房、結(jié)婚、生子已經(jīng)不再有那么強(qiáng)烈的“欲望”了,他們或許有想太多的弊病,但卻缺乏了與之匹配的行動力,有人索性就把“喪”作為標(biāo)簽,讓自己在這個標(biāo)簽里解釋通自己對現(xiàn)實(shí)所有的不抵抗,因?yàn)橥庠诘囊磺匈|(zhì)疑都可以用一句話去反駁:“因?yàn)槲冶緛砭秃軉拾 !?/p>
可是,從來如此,就是對的嗎?本來就很喪,就能讓自己所有的行動都成為必然嗎?對于那個讀者拋給我的問題,我現(xiàn)在其實(shí)想說,和世界的和解不是“佛系”或是對“喪”的妥協(xié)換來的,那只能叫你在現(xiàn)實(shí)面前的束手就降。和世界的和解是在與自我與社會的抗?fàn)幹幸稽c(diǎn)點(diǎn)地?fù)Q取個體的“自由”,而這一切都有代價,就像《鋼之煉金術(shù)師》里面的“等價交換”的定律。成長的代價是舍棄一部分的自我,舍棄一部分的偏執(zhí),去換取一部分的“自由”。
總在媒體面前嘻嘻哈哈的李誕成了“佛系”的符號,可是這只是他在這個媒體時代的社會人格罷了,那個在內(nèi)蒙獨(dú)自飲酒到微醺的年輕人,這個才是他最本我的狀態(tài),可是那個本我早被他殺死在最幽暗處了。他內(nèi)心足夠強(qiáng)大到殺死過去的自己的那一刻,才是他和這個世界最終的和解。所謂的和解,其實(shí)是自我抗?fàn)幒蟮慕Y(jié)果,而并不是無所作為的借口。
殺死過去的自己,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我們多少只愿意把最懦弱最脆弱的本我藏著掖著,隱瞞著,不去觸碰,顧左右而言他。
其實(shí)喪并不是一種非常糟糕的狀態(tài),我們大可不必視其為洪水猛獸,可是我們卻也不能在其中甘之如飴。你可以試著堅持做一件無關(guān)緊要的事,只為了簡單地從自己的舒適圈走出。你也可以無止境地去擁抱資本,把賺錢作為人生信仰。你可以讀書寫作,借助文字完成自我救贖。這一切,都是你和那個安逸的自我一點(diǎn)一滴進(jìn)行著抗?fàn)帯_@種點(diǎn)滴的水落,不會輕易化為空氣灰飛煙滅,它可以穿過最堅硬的石頭。胡適先生給人題詞,喜歡引用過《法華經(jīng)》的一個詞匯“功不唐捐”,意思就是所有的功德和努力并不會付諸東流,一切必有回響。
永遠(yuǎn)不妥協(xié),永遠(yuǎn)較勁著,大概就是你在喪中所需要的那一點(diǎn)點(diǎn)的牛逼勁兒。

經(jīng)授權(quán)轉(zhuǎn)載至數(shù)英,轉(zhuǎn)載請聯(lián)系原作者
作者:章程,野生建筑師,青年寫作者。豆瓣號:夜第七章。
作者公眾號:一點(diǎn)兒烏干菜(ID:NarratorZhang)
轉(zhuǎn)載請在文章開頭和結(jié)尾顯眼處標(biāo)注:作者、出處和鏈接。不按規(guī)范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未經(jīng)授權(quán)嚴(yán)禁轉(zhuǎn)載,授權(quán)事宜請聯(lián)系作者本人,侵權(quán)必究。
本文禁止轉(zhuǎn)載,侵權(quán)必究。
授權(quán)事宜請至數(shù)英微信公眾號(ID: digitaling) 后臺授權(quán),侵權(quán)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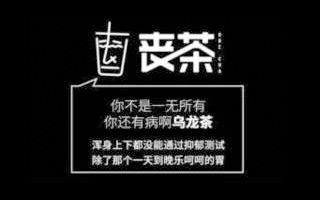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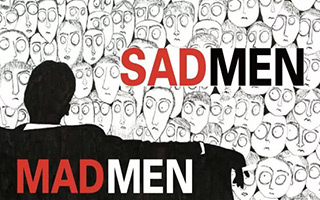





評論
評論
推薦評論
全部評論(3條)